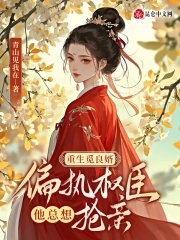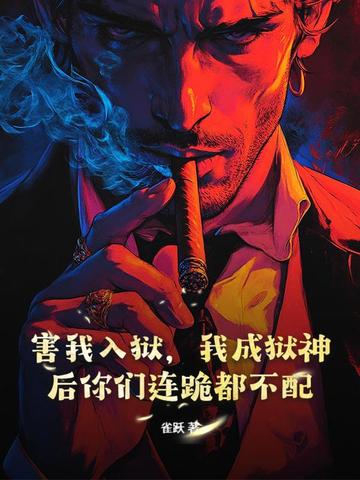第13章 意外收获
天工钱),要么被送去筛沙子"劳动学习"。
更常见的是在街头随意拦截盘查。农民工穿着沾满水泥点子的工服走在路上,突然就被喝令站住。联防队员翻着证件挑刺:"这照片不像你"、"印章模糊是假的",然后直接撕毁证件要求"补办"。有些联防队甚至在长途车站设卡,刚下车的农民工还没找到工作,就先被罚得身无分文。敢争辩的往往会被扣上"盲流"帽子,连人带行李塞进面包车拉到郊外丢弃。
这些行为背后是扭曲的"创收"机制——当时许多联防队的工资与罚款金额挂钩。农民工既无维权意识,又怕得罪"穿制服的",只能默默忍受。这种系统性欺压,成为那个年代农民工进城必须经历的"入门课"。
老张是个极其富有正义感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气得他不轻,知道这群闲散青年组成的联防队又在欺负没有暂住证的民工了,如果放到平常,敲诈民工点钱也就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竟然打起人来。
那时候,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怀揣着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却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遭遇了种种不公与欺辱。这些来自乡间的劳动者,往往被贴上“外来者”“低端劳动力”的标签,成为城市底层最脆弱的群体。
在建筑工地、工厂车间、街头巷尾,农民工的权益被系统性漠视已成常态。包工头肆意克扣血汗钱,工人们攥着皱巴巴的欠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简陋的工棚里挤着十几号人,发霉的被褥与裸露的电线交织成危险的生活图景;城市管理者挥舞着罚款单据,将摆摊谋生的小贩追得四处奔逃。更令人心寒的是,当这些皮肤黝黑的劳动者挤上公交车时,常有乘客掩鼻侧目,仿佛他们身上带着原罪般的污秽。
劳务市场门口蹲守的人群中,常混迹着以介绍工作为名的骗子;医院急诊室会先查验他们的暂住证才肯施救;就连子女想进公办学校,也要面对借读费的高墙。某些私营企业主将农民工视为“会说话的机器”,工伤致残后往往用几千块钱打发回乡。每当春节前后的讨薪潮涌起,总有人爬上塔吊以命相搏,这些极端场面背后,是无数被碾碎的尊严。
这种集体性歧视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惯性,也掺杂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农民工用双手托起了城市的天际线,自己却活在社会保障的阴影里。他们像候鸟般穿梭于城乡之间,既不被城市真正接纳,又难以回归熟悉的乡土,成为工业化浪潮中最沉重的注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573321字06-26
- 国姓窃明
- 3780952字06-26
- 重生觅良婿,偏执权臣他总想抢亲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山见我在)的经典小说:《重生觅良婿,偏执权臣他总想抢亲》...
- 428654字06-25
- 害我入狱,我成狱神后你们连跪都不配!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雀跃)的经典小说:《害我入狱,我成狱神后你们连跪都不配!》...
- 365392字06-30
- 综漫:从龙珠出包开始修仙之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念起寒舍)的经典小说:《综漫:从龙珠出包开始修仙之旅》最...
- 1967220字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