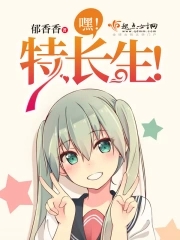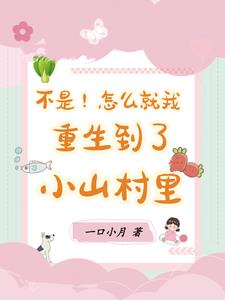第269章 长夜微火
和一把小小的木质算盘。他这才缓缓站起。不同于前面几位汇报者,他站得有些局促,带着一种小知识分子特有的谨慎和惶恐。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镜片裂了一条缝的塑料框眼镜,摊开那个笔记本,翻到夹着纸片的一页,然后又郑重其事地拿起那把算盘,仿佛要给自己一个计算精确的信心保障。
“老……老大……”他开口,声音不像林强军那么洪亮,也不像覃龙那么急躁,更不像鬼子六那么阴冷,他声音天生带点微颤,此刻更因为环境压力而显得更加发虚。“现在,我汇报一下我们……组织财务状况的最新情况。” 他特意强调了“组织”二字,似乎想用这个词的正式感来抵消他内心的不安。
他习惯性地清咳一声,目光紧盯着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符号,像是抓住救命的稻草。
“我们目前执行的薪酬体系,严格按照您亲自制定的‘最大受益’工资发放标准。”他说到这里,带着无比严谨的态度,似乎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确认。
“这个标准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其一,基本保障性工资。每人每月固定的口粮钱,最低不少于本地临时工水平,用于确保基本生存。
其二,业绩提成。这部分按照其负责的片区订单成功完成和资金安全回收总额的固定比例(此处他精确报出了内部设定的分层比例)提取,多劳多得。
其三,计件提成。每一件成功、安全送达的订单,不论大小、价值高低,都有固定的单数补贴。跑得多,补贴就多。”
何博文的手指下意识地在算盘上一拨,发出轻微但清晰的“哒”声,仿佛在无声地为自己打气。
“经过本月初的工资发放和统计结算,目前我们所有在籍成员的最低月收入(仅含基本工资及保底计件提成)……”他吸了口气,目光快速扫过纸上的数字,“已经稳定达到了十五块钱人民币一个月。” 十五块!这在农村,尤其是普遍收入极低的七十年代中期,对一个“灰色”组织的底层成员而言,绝对是一笔能支撑家计、甚至能让家人吃饱穿暖的“稳定”收入了!这个数字出口,房间里再次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不少人的脸上泛起一丝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和希望的光彩。
何博文显然也感受到了这股情绪的波动,但他没有停下,语速反而略微加快了些,透出报告重点的急迫:“在此基础上,加上各级管理津贴(您规定不可高于成员最高收入的2倍)、各环节的必要损耗补贴、设备租金(如藏身的库房)、固定办公点(如临时联络站)的租金、用于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9页 / 共11页
相关小说
- 普通人的重生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什么名不吃饭)的经典小说:《普通人的重生日常》最新章节...
- 1809326字07-29
- 戏假成真:演瘾君子这么像?查他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本正经胡写)的经典小说:《戏假成真:演瘾君子这么像?查...
- 4876807字07-27
- 吞噬星空:重生雷龙皇,多子多福
- 2611188字03-15
- 嘿特长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郁香香)的经典小说:《嘿特长生》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1064124字07-19
- 不是!怎么就我重生到了小山村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口小月)的经典小说:《不是!怎么就我重生到了小山村里》...
- 1162626字07-30
- 愚人的图书馆
- 1803419字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