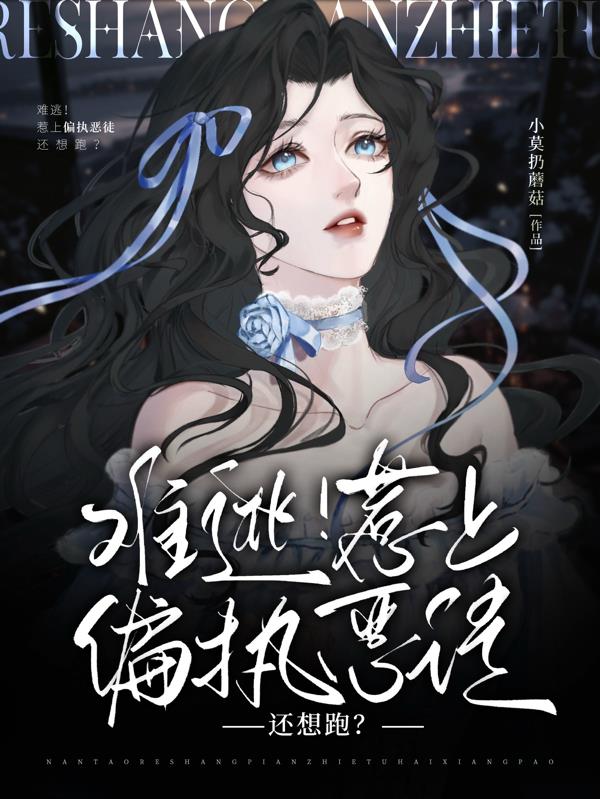第377章 和田:和玉之都,丝路之光
“卡瓦甫”的酸奶冰饮,又吃了一串刚出炉的“皮牙子烤肉”。一边吃,一边听摊主讲他祖父的故事——曾是驼队商人,往返于和田与喀什之间,靠着脚掌与记忆丈量沙海中的驿路。
我继续走入深处,发现一个小舞台。此刻正有年轻人表演热瓦甫与冬不拉演奏,节奏跳跃,旋律如风。我站在人群中,看着男女老少跟着节拍起舞,脑中仿佛回荡起整个塔里木盆地的韵律。
我写下:
“和田的夜,是一场不打草稿的交响曲,民族的琴弦,拨动的是千年的和声。”
清晨,我走访了一所和田本地的多民族小学。校园不大,孩子们正背着小书包,鱼贯而入。我被一位女教师邀请进去,她是汉族,已在和田教书十余年。
“这儿的孩子特别纯粹,”她笑着说,“他们一边讲维吾尔语,一边也能用普通话朗读《论语》。”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他们念诗,写字,唱歌,跳舞。不同肤色、不同眼神,却都在一方课堂上共享知识的阳光。
课后,一个叫古丽的女孩悄悄问我:“你是来写书的吗?能写我们的学校吗?”
我点头,她眼睛亮了起来,“那请你写上我们有多爱这里。”
我郑重地在笔记中写下:
“和田的绿洲,不只是农田与果园,更是孩子们心里播种希望的学堂。”
离开城区,我骑车来到一座古老的清真寺。此地远离喧嚣,四周环绕着枣林、胡杨与红柳。寺门外,一位白胡子的伊玛目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看到我来,他点头示意。
我脱鞋进入殿内,肃穆之感油然而生。拱门斑驳,地毯洁净,墙面绘有繁复花纹与经文。片刻后,几个村民陆续进来,跪地祷告,动作缓慢而庄重。我没有打扰,只静静坐在后方,听着他们口中吟诵着我听不懂却能感受到平静的诗句。
出了殿,我又随他们一起去附近枣林浇水,修渠,搬石头。谁说信仰只是神圣?他们将信仰揉进劳动,揉进每一顿饭、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手掌接触泥土的瞬间。
我站在老城区外的一段古道旁,那是一条丝绸之路南线旧迹,被风沙掩埋又被考古人重新揭出。
脚下的每一块碎砖,每一粒沙土,都可能是商旅驼铃经过之处。我在路边捡起一块写有波斯文字的陶片,想象它曾随某个波斯商人跨越昆仑,带着香料、玻璃、锦缎,来到这里,换走玉石、驼皮、葡萄干与故事。
如今这些故事只剩尘土,但我知道,在地球交响曲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赶海:我靠赶海养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我只想当一名肥宅)的经典小说:《赶海:我靠赶海养娃》最新...
- 2274968字07-19
- 茅山讨债人
- 707743字07-30
- 戏假成真:演瘾君子这么像?查他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一本正经胡写)的经典小说:《戏假成真:演瘾君子这么像?查...
- 4876807字07-27
- 普通人的重生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什么名不吃饭)的经典小说:《普通人的重生日常》最新章节...
- 1809326字07-29
- 难逃!惹上偏执恶徒还想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莫扔蘑菇)的经典小说:《难逃!惹上偏执恶徒还想跑?》最...
- 437735字07-19
- 我把家乡打造成人间仙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鲤戏猫)的经典小说:《我把家乡打造成人间仙境》最新章节全...
- 7073087字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