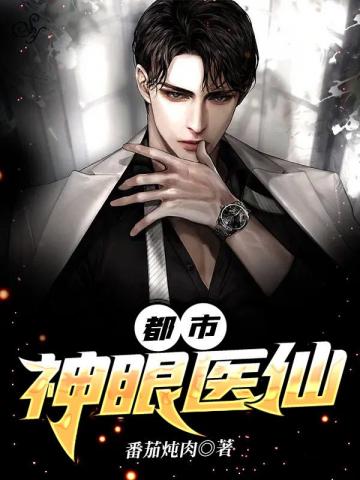第219章 春雷起,震山河!
着刮着……终于卷到了京城城墙根儿下……
新华社的大院里炸开了锅。
一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编辑部主任,拿着刚批下来的采访任务单,激动得手指头敲桌子:“老刘!小王!你们几个老笔杆跑一趟西北!”
“记着,把眼睛瞪圆了!”
“好经验要报足,有啥沟沟坎坎的也甭藏着掖着!老百姓的肚子等不得瞎话!”
几个资深记者心领神会,麻利地收拾帆布挎包、黄书包,采访本上早就密密麻麻列好了几页问题。
他们太知道这颗“卫星”的分量了。
农科院的小会议室更是争得面红耳赤。
白发如银的老专家吴教授,指着墙上那幅色彩斑驳的全国地图,手都在颤:“活生生的例子摆在这儿了!天大的好事!可正因为它太好了,才更得慎之又慎!”
“想想五十年代末的教训!得摸索,得稳步来!千万……千万不能一窝蜂!”
旁边的年轻助手刷刷地记,心里也绷着弦。
这股风,早就钻透了围墙,吹进了最日常的角落……
农大的教室里,老教授临时改了教案,对着讲台下学生们惊愕又兴奋的脸,讲起了黄土高原上的奇迹。
农场的会计室里,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山响,算着如果自家的地也增产,能多发多少粮票……
天南地北反应不一!
有的地方县干部揣着介绍信已经挤上了开往西北的火车;有的地方还在观望,领导眉头紧锁,让手下“再研究研究”。
还有的地方,私下里冷言冷语。
“哼,搞包产?那叫什么主义?”
“步子大了,不怕扯着淡?”。
可甭管上头怎么琢磨,街头巷尾的茶馆里、田间地头的垄沟边、井台旁的树荫下,到处都在传、都在叹、都在算。
“听说了没?西北有个弯河村,麦子打出了天量!”
“四百五十五斤啊!那地里埋了金娃娃?”
“隔壁老王昨儿拿报纸回来,手都是抖的!他家六口人,去年分的麦子连腊月的白面饺子都没吃上……”
“要是咱们这地头也能这样……”
“敢想啊!顿顿白面馍馍,白花花的那种!神仙过的日子!”
“快看看吧,听说中央都惊动了……”
弯河大队的经验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整个国家上空!
没人是傻子,都知道这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710795字07-24
- 普通人的重生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叫什么名不吃饭)的经典小说:《普通人的重生日常》最新章节...
- 1809326字07-29
- 开局抱上魔尊大腿,开启摆烂人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湘侞)的经典小说:《开局抱上魔尊大腿,开启摆烂人生》最新章...
- 1316443字03-12
- 都市神眼医仙
- 我是老中医,专治各种吹牛逼!我武道超神,吊打一切不服气!秦飞偶得神秘传承,拥有神...
- 8341756字10-16
- 上都城来了个狐狸精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赢香)的经典小说:《上都城来了个狐狸精》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627697字10-29
- 宝可梦之我不做男人啦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芝士X年糕)的经典小说:《宝可梦之我不做男人啦》最新章节全...
- 1414956字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