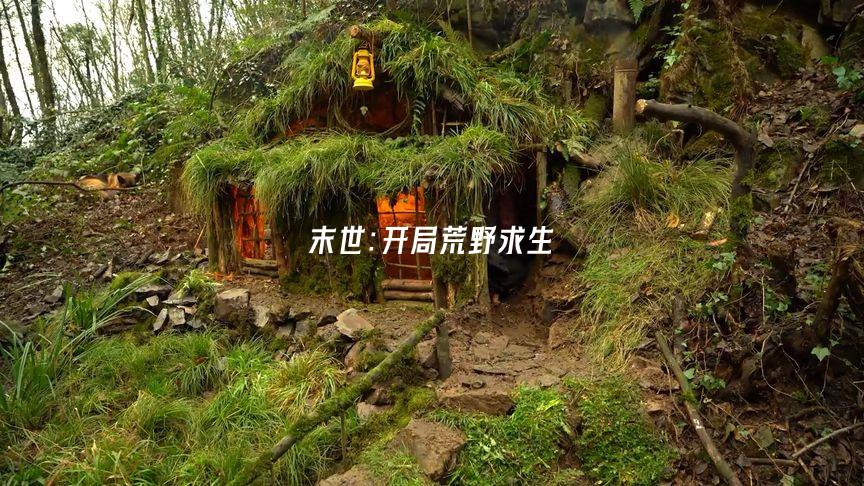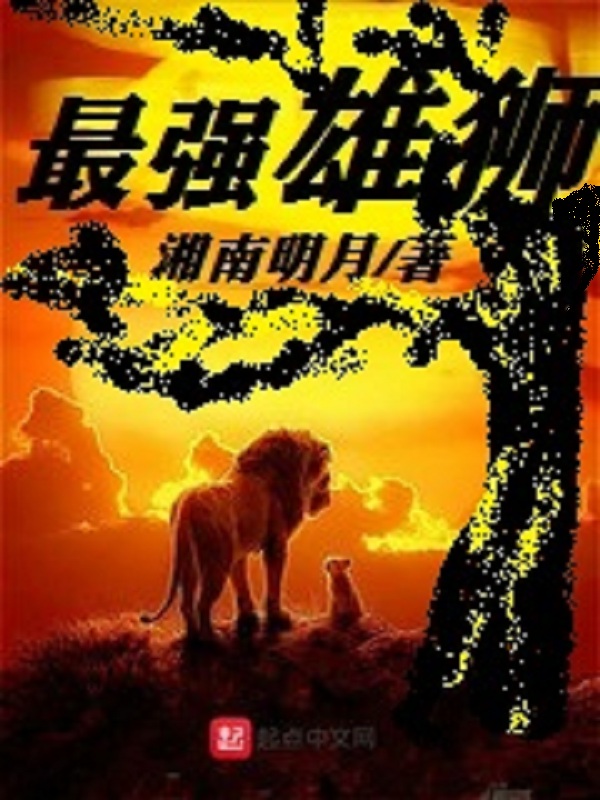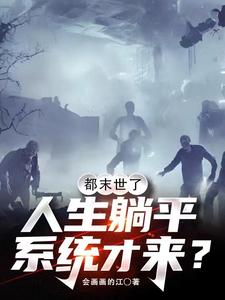第4章 龙泉剑鸣惊霜晨
家祖上留下的《铸剑火候诀》。“去年小吴把这图扫描进电脑,”老陈粗糙的手指抚过绢布上的虫蛀痕迹,“AI算出了十九种淬火方案,可最准的还是老辈人‘看火色、听水音’的土法子。”
晚晴的相机捕捉到绢布与电脑屏幕重叠的瞬间,古老的朱砂笔触在蓝光中微微发烫。许砚秋忽然意识到,所谓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像老陈这样的匠人,愿意把掌心的温度传递给触碰键盘的年轻人——就像陆辰安现在正把《铸剑火候诀》里的“子时淬火忌惊”,转化为小说中凶手利用更夫打更声掩盖罪行的诡计。
归程经过剑池畔,陆辰安忽然停步。月光在水面碎成万千银鳞,他望着自己倒映在水中的影子,忽然轻笑:“我懂了!小说里的‘剑魂诅咒’不是迷信,是凶手利用淬火时的金属应力变化,让剑在特定温度下断裂——就像老陈说的,‘急火出次品,慢工藏杀招’。”
手机在裤兜震动,母亲发来语音:“今天去医院查了眼,大夫说老花眼要戴新眼镜了,别担心,你爸当年编县志时也戴过双圈的。”附带的照片里,老人举着新买的金丝眼镜,镜腿上系着许砚秋小时候编的红绳——那是他中学时在劳技课做的手工艺品,没想到母亲竟保存了二十年。
深夜,许砚秋在民宿书桌前整理素材,听见隔壁陆辰安的房间传来键盘敲击声。推开窗,山风送来若有若无的剑鸣,混着远处铸剑坊未熄的炉火气息。他忽然想起老陈说的“每把剑都在等懂它的人”,笔下的文字又何尝不是?那些在稿纸上反复锤炼的句子,那些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平衡的时刻,都是为了让故事成为照亮人心的“刃”,而非迎合市场的“装饰品”。
周明宇的消息在这时发来:“徽州木雕传承人老汪摔断了右手,现在用左手教徒弟,你带陆辰安去看看?”许砚秋望向案头摊开的《营造法式》,书页间夹着老陈送的剑穗——用铸剑余料打成的银饰,刻着极小的“慎终如始”四字。他知道,下一站的徽州之行,将会遇见更多关于“残缺与传承”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终将织就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心长卷”。
窗外,龙泉的星空格外清亮,每颗星子都像匠人手中永不熄灭的炉火。许砚秋提起笔,在新稿纸上写下:“老陈把断剑插进剑池的瞬间,水面倒映的银河忽然碎成万千光斑。他说这是剑在向天地问路,而我们写作者,何尝不是在每个字里,向自己的良心问路?”
墨色在稿纸上晕开,如同老陈淬火时腾起的水雾。在这个追求“快速锻造”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末世:开局荒野求生
- 末世:开局荒野求生是由作者张秋枫著,免费提供末世:开局荒野求生最新清爽干净的文...
- 2589681字04-28
- 最强雄狮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湘南明月)的经典小说:《最强雄狮》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432497字07-24
- 都末世了,人生躺平系统才来?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会画画的江)的经典小说:《都末世了,人生躺平系统才来?》最...
- 2115503字07-30
- 末世:美女太多,别墅住不下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我就是混子)的经典小说:《末世:美女太多,别墅住不下了》最...
- 605259字10-20
- 求生:从茅草屋开始踏上巅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棠梨煮雨)的经典小说:《求生:从茅草屋开始踏上巅峰》最新...
- 476649字11-30
- 杀神快跑,你对象玩狙的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明路星)的经典小说:《杀神快跑,你对象玩狙的》最新章节全文...
- 1221019字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