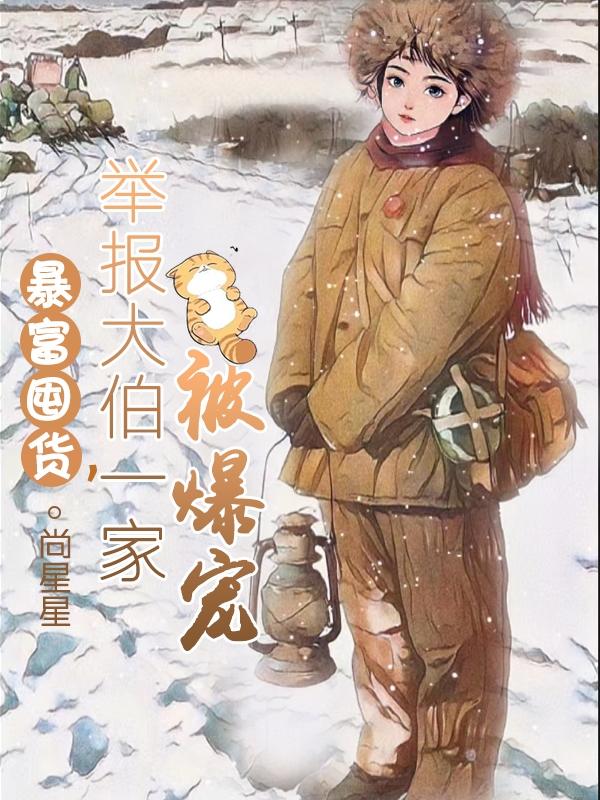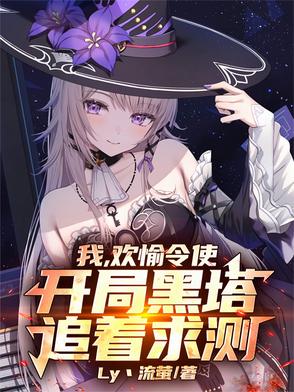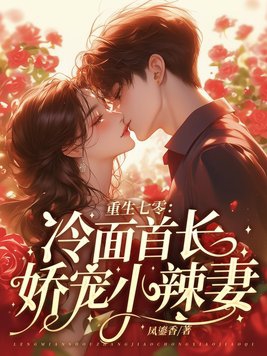第226章 编钟秘辛:探寻生辰八字背后
>
接下来的三天,赖诗瑶像根绷紧的弦。
她一边担心编钟刻痕背后的秘密,一边又对即将到来的音乐会充满期待。
陈教授的实验室在郊区,她每天往返两小时送检测样本;合作方虽然妥协,但巡演场地需要重新确认;更糟的是,网上突然冒出帖子——“非遗音乐会用赝品编钟,专家:音色全靠后期修音”。
帖子配图是编钟局部照片,配文是“懂行的都知道,真编钟不可能这么亮”。
评论区瞬间炸了:“怪不得听着像电子音”“赖诗瑶炒作非遗,实际是商业骗局”“郝家兄弟捧人也太没底线了”……
赖诗瑶盯着手机,指甲掐进掌心,感觉尖锐的疼痛。
她联系了三家媒体做直播鉴定,可网友说“媒体收了钱”;她请文保所出证明,有人说“文保所和她爸是老同事,肯定护短”。
直到第四天清晨,她在后台看见击磬老人蹲在编钟前,用枯枝在地上写字——“我来。”
老人耳聋,但年轻时是故宫古乐器修复师,手上的老茧比编钟的铜锈还厚。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鹿皮,轻轻擦拭钟壁,发出轻柔的摩擦声。
又从怀里摸出个铜制小锤,敲了敲最上层的“宫”钟。
清越的钟声在后台回荡,如同悠扬的仙乐。
他指着钟身上细密的冰裂纹,又比划着自己的耳朵——真编钟的裂纹是自然形成的,仿品的裂纹太规则;真编钟的余震能持续十三秒,仿品最多七秒。
他又掏出本泛黄的笔记本,翻到1987年的记录页,上面贴着父亲的签名——“赖建国,参与编钟修复”。
老人指着“赖建国”三个字,又指向赖诗瑶,重重点头。
直播镜头对准笔记本时,评论区突然安静了。
有人翻出老人当年修复故宫编钟的新闻,有人算出钟声余震确实十三秒,还有人说“冰裂纹的照片我在博物馆图录里见过”。
谣言像退潮的海水,转眼间只剩零星几句“阴谋论”。
赖诗瑶蹲在老人身边,握住他粗糙的手,那粗糙的触感如同岁月的纹路。
老人冲她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三十年的光阴,像口装满故事的井。
“诗瑶。”郝宇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她熟悉的沉郁,如同低沉的乐章。
“监控室说,最近三天有个穿黑风衣的人在附近转悠,没拍到正脸。”他递给她个证物袋,里面装着张名片,“今天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暴富囤货,举报大伯一家被爆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尚星星)的经典小说:《暴富囤货,举报大伯一家被爆宠》最新章...
- 1387216字06-06
- 我,欢愉令使,开局黑塔追着求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Ly丶流萤)的经典小说:《我,欢愉令使,开局黑塔追着求测》最...
- 1026513字05-23
- 长跑八年,婚礼现场她奔向白月光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超萌萨摩耶)的经典小说:《长跑八年,婚礼现场她奔向白月光》...
- 1258586字06-03
- 重生七零:冷面首长娇宠小辣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凤鎏香)的经典小说:《重生七零:冷面首长娇宠小辣妻》最新...
- 691848字04-25
- 陆总别作,太太她不要你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是空空呀)的经典小说:《陆总别作,太太她不要你了》最新章节...
- 364175字06-04
- 开局桥上救下轻生女,系统激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漠星凡)的经典小说:《开局桥上救下轻生女,系统激活》最新章...
- 2208297字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