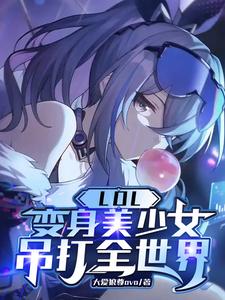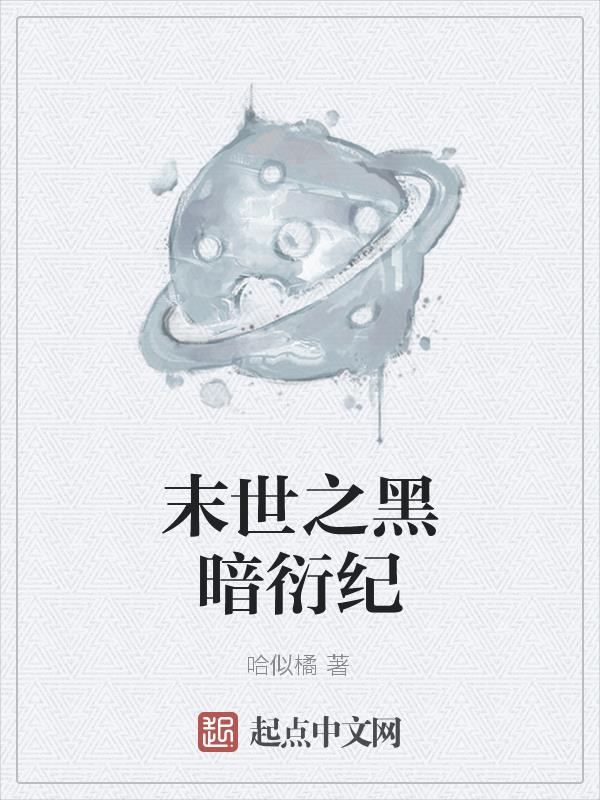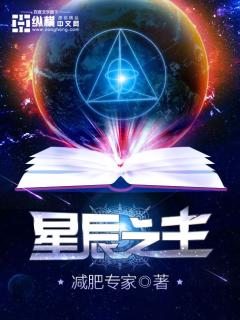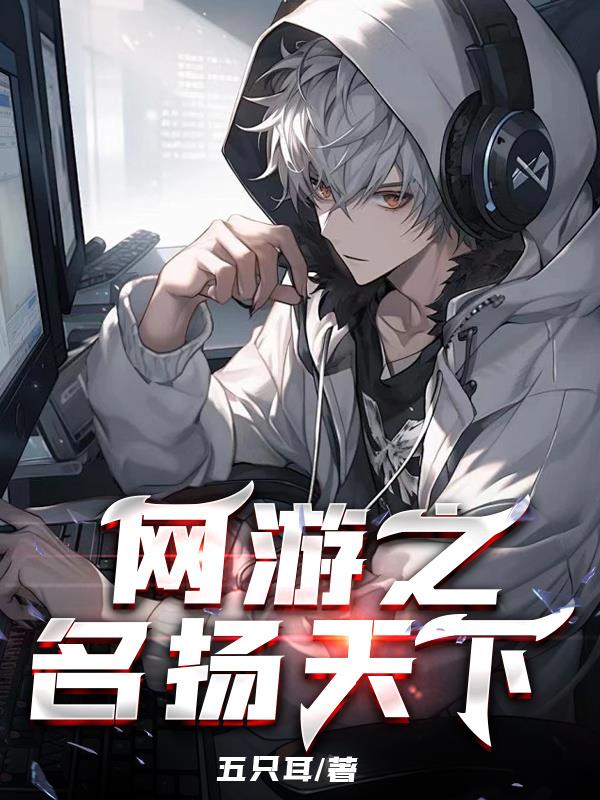《南岭芪韵:黄精医者传》下卷
阿石常说:“师父讲过,病像山里的云,时时在变,药也得跟着变。”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这年冬天,南岭下了场罕见的大雪,积雪压塌了好几户人家的柴房。更糟的是,雪后气温骤降,不少人冻得手脚生疮,还发起高烧,连烧几天不退,身上出了不少红疹。
“这是‘寒毒郁表’,”阿石翻着师父的竹简,上面没有现成的方子。他想起师父说过“黄芪能托毒外出”,便试着用生黄芪配麻黄、桂枝、连翘,想让寒气从表而出,热毒随汗而解。可试了几个人,效果并不明显,有的人还开始呕吐。
阿石急得睡不着,夜里独自跑到屋后的黄芪地。雪地里的黄芪早已枯萎,只剩下埋在土里的根。他蹲在地上,抚摸着冻硬的泥土,喃喃自语:“黄芪啊黄芪,师父说你有灵,现在村里有难,你帮帮我吧……”
说着说着,他忽然发现,雪地里有几株黄芪的根竟从土里露了出来,根须上还沾着些黑色的泥土。阿石心里一动,想起鹰嘴崖的土壤是偏沙性的,而屋后的土偏黏,这几株露根的黄芪,莫不是在提醒他什么?他赶紧挖起一株,切开根来看,发现这株黄芪的根心比别的更黄,闻着也更香浓。
“难道是……”阿石想起师父说的“土性不同,药性有别”。他把这几株露根的黄芪切片,配了些生姜、葱白,又加了少量黄连,煎成药汤。这次,喝药的人很快就出了汗,烧也退了,红疹也慢慢消了。
“是你在帮我,对不对?”阿石对着黄芪地轻声说。第二天,他发现雪地里的黄芪根又多露出了几株,像是在回应他。从那以后,阿石更信草木有灵了。他采药时总会先拜一拜,采挖时留下三分之一的根,让它们能重新生长;炮制时严格按照师父教的方法,从不敢偷懒。
有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得了“消渴症”,喝多少水都觉得渴,人也瘦得脱了形,找了很多大夫都没治好。他听说南岭的阿石大夫医术高明,便特意找来。阿石看他舌红少苔,脉细数,是“阴虚燥热”,可师父说过黄芪性温,阴虚的人用了会上火。
他犯了难,夜里又去看黄芪。月光下,他发现有几株黄芪的旁边长着枸杞,枸杞是滋阴的。阿石忽然明白了:“药有相生,黄芪性温,配滋阴的枸杞,不就既能补气,又不助火了吗?”他用黄芪配枸杞、知母、葛根,给商人煎药。三个月后,商人的消渴症竟好了大半,临走时给阿石送了块银子,阿石却婉拒了:“我师父说,行医是为救人,不是为赚钱。你若真想谢我,就多帮帮穷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虹猫蓝兔七侠后传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岬新涂)的经典小说:《虹猫蓝兔七侠后传》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939122字05-12
- LOL:变身美少女,吊打全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大爱狼尊ovo)的经典小说:《LOL:变身美少女,吊打全世界》最...
- 628791字07-25
- 末世之黑暗衍纪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哈似橘)的经典小说:《末世之黑暗衍纪》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2808004字09-10
- 星辰之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减肥专家)的经典小说:《星辰之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8819801字07-28
- 巨兽求生战场:开局获得幸运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蛙鱼塘下)的经典小说:《巨兽求生战场:开局获得幸运七!》...
- 2345600字05-29
- 网游之名扬天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五只耳)的经典小说:《网游之名扬天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580357字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