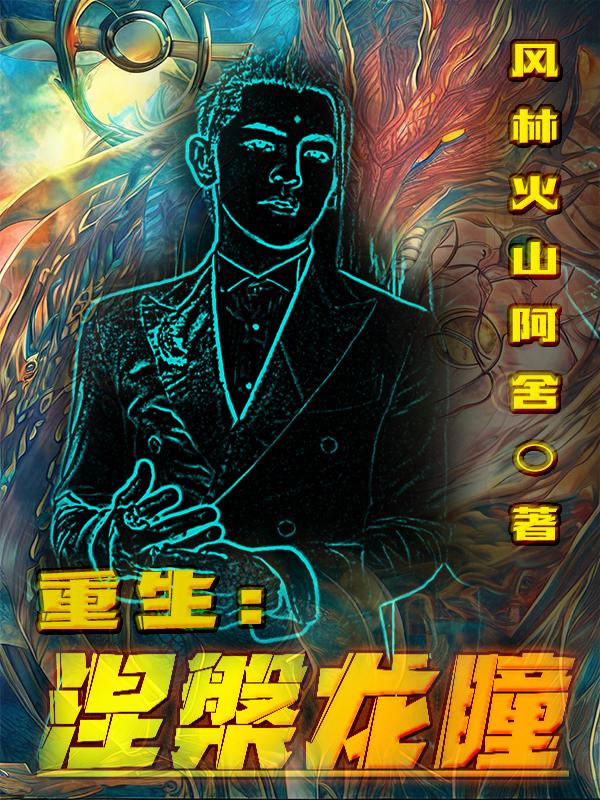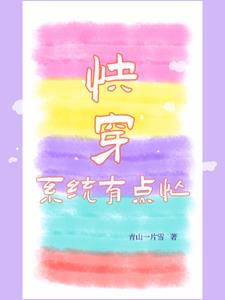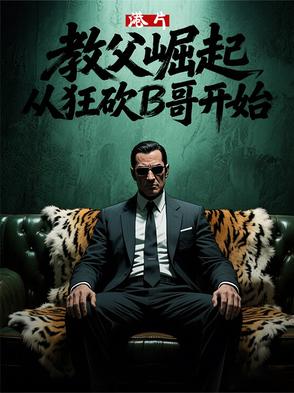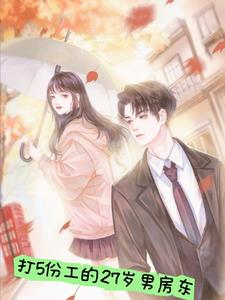第463章 大赦天下
根红绳系着,手里攥着张户籍文书,纸边都磨卷了。 “张阿婆,八十三了?”
小吏核对着文书,笔尖在簿子上划过,发出 “沙沙” 的声响。
老婆婆点点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哼:
“托圣人的福,还能走得动。”
旁边的后生忙补充:
“家母去年还能纺线呢,就是眼睛花了。”
小吏笑着应:
“领了布帛,让您孙媳妇给您做件新棉袄。”
粟米装在陶罐里,每个老人一罐,沉甸甸的压手。
李老汉接过罐子时,手指触到陶土的粗粝,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太宗皇帝征高句丽那年,他也是在这街上领过救济粮,只是那时的罐子要小些。
“多了半罐呢。”
他跟旁边的王老汉嘀咕,王老汉的牙掉得只剩两颗,咧着嘴笑:
“新皇后册立,圣人高兴呢。”
布帛是粗麻布,浆洗得发硬,却比家里织的细密。
赵阿婆把布帛搭在胳膊上,布角扫过手腕,痒得她直笑。
她的重孙子才三岁,正抓着布帛的边角往嘴里塞,后生忙拉开:
“这是给太婆做衣裳的,不能吃。”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笑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进了晒着的谷堆里。
城门口的告示牌前围满了人,一个识字的秀才正高声念着诏书:
“…… 鳏寡孤独皆有赡养,残障者由官府供给衣食……”
人群里发出啧啧的赞叹,一个瞎眼的老汉摸着身边的竹竿,喃喃:
“赶上好时候了。”
他的竹竿头上包着块破布,是去年冬天冻裂了,街坊给缠的。
坊市的角落里,几个曾被判流放的汉子正收拾行李。
一个脸上带疤的汉子把件旧棉袄塞进包袱,那是他在牢里穿了三年的,补丁摞着补丁。
“去岭南还是回老家?”
旁边的人问他。他摸了摸疤,那是当年打架留下的:
“回老家,给我娘上炷香,她总说我不成器。”
日头升到正午,棚子里的粟米和布帛渐渐少了。
户部的小吏们开始收拾摊子,木尺和账簿被装进布包,地上散落着些谷粒,引来几只麻雀啄食。
一个老吏数着剩下的布帛,忽然说:
“比去年多了三成呢。”
另一个接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重生:涅盘龙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风林火山阿舍)的经典小说:《重生:涅盘龙瞳》最新章节全文...
- 2619080字06-13
- 御兽:宠兽养家我有钱花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周周然)的经典小说:《御兽:宠兽养家我有钱花》最新章节全...
- 1153027字07-18
- 系统的快穿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山一片雪)的经典小说:《系统的快穿日常》最新章节全文阅...
- 965995字07-03
- 港片:教父崛起,从狂砍B哥开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氛)的经典小说:《港片:教父崛起,从狂砍B哥开始》最新章...
- 1103152字07-06
- 打5份工的27岁男房东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紫苏土豆)的经典小说:《打5份工的27岁男房东》最新章节全文...
- 1434148字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