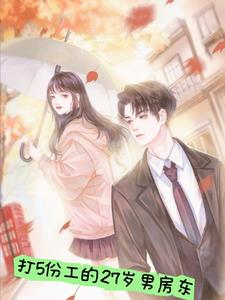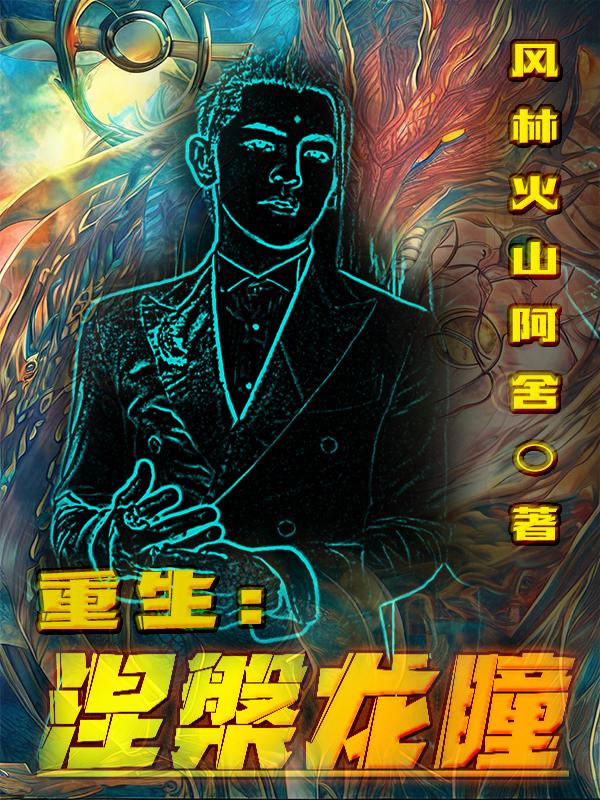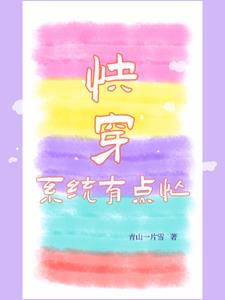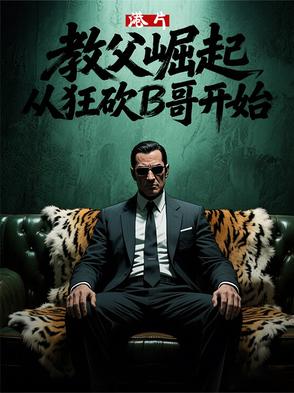第451章 崔敦礼任中书令
四岁入秦王府做记室,到如今站在紫袍队列里,鬓角的白发比同僚们密得多,像是落了层早霜。
叩首时,腰间悬着的金鱼袋撞在金砖地面上,发出厚重的闷响 这鱼袋是贞观年间因守凉州有功得的,边角已被摩挲得发亮,袋里的鱼符是用密州进贡的玳瑁磨的,凉丝丝地贴着皮肉。
“臣崔敦礼,谢陛下。”
他的声音带着些微沙哑,尾音还有点发颤。
这是永徽元年在凉州抵御突厥时落下的毛病,那年冬天雪下得格外大,他在城楼上守了整三个月,回来后就总这样,阴雨天更甚。
内侍展开诏书的瞬间,殿外的蝉鸣恰好在此时涌进来,聒噪得让人心头发闷。
黄麻纸卷轴上,“崔敦礼任中书令” 七个字用朱砂写就,笔锋遒劲,是起居郎褚遂良的笔迹。
旁边用蝇头小楷注着 “仍兼检校太子詹事”,墨迹稍浅些,该是昨夜才补上去的。 站在一旁的来济微微颔首,眼角的余光扫过崔敦礼微驼的脊背。
他想起贞观十七年两人共掌吏部时,这位老臣总爱在退朝后留在官署,把堆积的选官册按籍贯分类,用不同颜色的绳捆好,连册页边角的卷折都要一张张捋平。
那时来济还笑他太过较真,崔敦礼只说:
“文书乱了,人心就乱了。”
退朝后,崔敦礼没回府邸,径直往中书省去。
穿过月华门时,守门禁军给他行礼,他认出领头的校尉是当年凉州旧部的儿子,肩上还留着和他父亲一样的箭疤,便多问了句:
“你父亲的腿疾好些了?”
校尉红了脸,说上个月刚领了朝廷发的药,能下地走路了。
中书省的值房还留着前任的痕迹。
案几上堆着未发的敕令,最上面那份是岭南獠人纳贡的清单,墨迹已干,边缘却被人用朱笔圈出几处 “象牙二十根” 旁标着 “应验成色”,“犀角十枚” 后写着 “需核对产地”。
崔敦礼拿起翻了翻,见是自己当年教过的小吏所写,嘴角牵起一丝浅淡的笑意。
“把我的官印取来。”
他解开朝服腰带,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布衫,那是夫人去年用他旧袍改的。
属吏很快捧着印盒回来,铜质的印身刻着 “中书令” 三个字,边角的毛刺还没磨掉,是今早从尚宝局领的新物。
他蘸了朱砂,在废纸上盖了个印蜕,见字迹清晰,便推到一旁。
“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打5份工的27岁男房东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紫苏土豆)的经典小说:《打5份工的27岁男房东》最新章节全文...
- 1434148字07-03
- 重生:涅盘龙瞳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风林火山阿舍)的经典小说:《重生:涅盘龙瞳》最新章节全文...
- 2619080字06-13
- 御兽:宠兽养家我有钱花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周周然)的经典小说:《御兽:宠兽养家我有钱花》最新章节全...
- 1153027字07-18
- 系统的快穿日常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山一片雪)的经典小说:《系统的快穿日常》最新章节全文阅...
- 965995字07-03
- 港片:教父崛起,从狂砍B哥开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氛)的经典小说:《港片:教父崛起,从狂砍B哥开始》最新章...
- 1103152字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