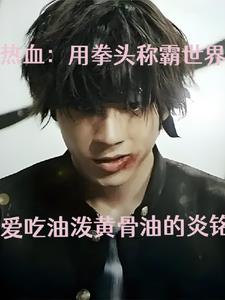第178章 音乐无国界第一步
胡逸接着说:“所以我的想法是,每个国家都单独做个需求评估。”胡逸把平板打开,找出三张地图来。他说:“A国缺基础乐器,还得给教师搞搞培训;B国呢,要是能让本土音乐人参与合作,抵触情绪估计就能少点;C国……”他的手指停在C国地图上,“从流动音乐教室入手应该行,不过得绕开那些有武装冲突的地方。”
大卫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镜片后面的眼神变得温和了些,说:“您对‘因地制宜’的理解比我想的要深啊。”说完就把文件合上了,又接着讲:“可A国是第一个试点,他们的教育部门对国际援助一直都特别谨慎。A国教育部文化司司长是玛丽·约翰逊女士,我觉得您今天就得飞到A国去。”
A国首都的机场就像个被岁月折腾得破旧不堪的老玩具。
胡逸拉着行李箱走下舷梯的时候,一股夹杂着尘土的热浪直往脸上扑。远远地能看到一群又黑又瘦的孩子追着行李车跑呢,有个孩子手里举着个用铁皮罐做的“鼓”,正拿着树枝敲得像模像样的。
玛丽的办公室在教育部大楼的顶楼,百叶窗拉得死死的,空调嗡嗡作响,声音特别刺耳。
这位穿着藏蓝色西装的女官员把咖啡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放,说道:“胡先生,A国每年都要接待27个国际援助项目呢。去年有个组织捐了三百台钢琴,结果因为没电,三分之二都成了破铜烂铁。”
她从一堆东西里抽出一份资料,“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这正是胡逸近三年的资金流向表,就是大卫之前要求提供的那份证明。“你的钱都是从演唱会、广告代言,还有粉丝应援这些地方来的。”玛丽一边用指甲敲着纸张,一边说道,“我咋能知道,你不是来给新歌炒作热度的呢?”
胡逸突然就想起了出发之前翻出来的那张旧照片。
他伸手从西装的内袋里摸出了一个塑封袋,那张泛黄的照片里,十六岁的他正站在琴行的玻璃柜前面呢。他的鼻尖紧紧贴着那冰凉的玻璃,眼睛亮晶晶的,就那么望着柜子里的红棉吉他。那可是他在琴行当了三个月杂工,却连琴盒都没机会摸一下的宝贝啊。
“我十三岁的时候,在二手市场捡到了一把断了两根弦的吉他。”他把照片推了过去,“琴头上刻着‘赠小逸,未来是你的舞台’,后来才晓得是老板偷偷刻上去的。那把琴陪着我熬过了高考之前那种崩溃的日子,我还在出租屋漏水的阳台上用它写了第一首歌呢……”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透视不赌石,你又在乱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迟暮流年)的经典小说:《透视不赌石,你又在乱看》最新章节全...
- 4147110字04-17
- 你透视眼不去赌石,乱看什么呢!
- 【小人物逆袭+透视+赌石+鉴宝+捡漏+神豪】秦朝阳,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社会晃荡两年...
- 3795767字10-02
- 热血:用拳头称霸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爱吃油泼黄骨鱼的炎铭)的经典小说:《热血:用拳头称霸世界...
- 711248字12-20
- 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微茫的砂砾)的经典小说:《战神王爷夜夜来爬墙,王妃她怒了》...
- 1244383字06-14
- 影帝捡到软糯白月光
- 601418字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