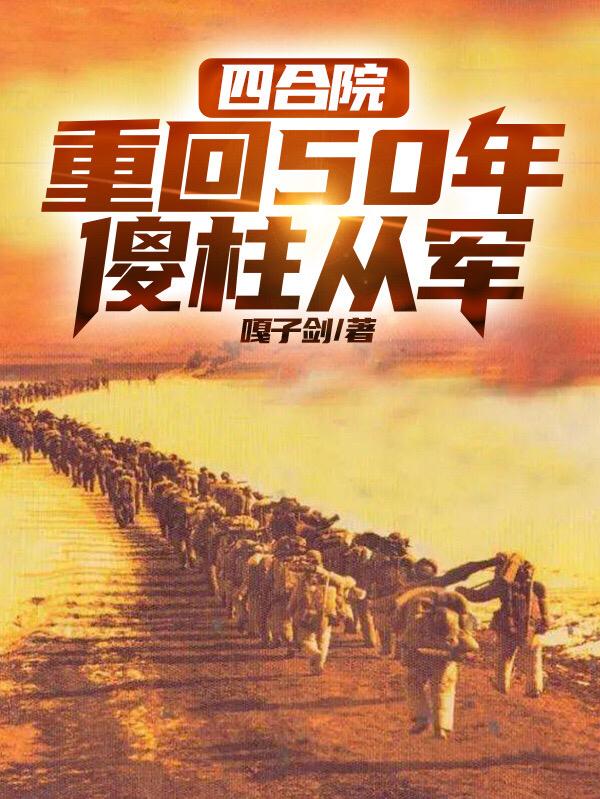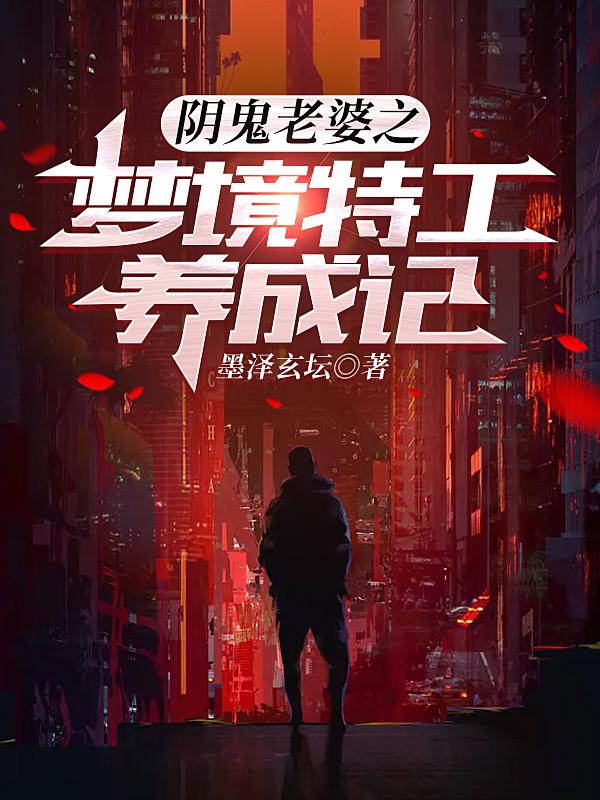第505章 显眼知青
和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一起,把汗水洒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想到这里,孙玄的嘴角微微上扬,沉沉睡去。
1968年9月1日凌晨,孙玄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玄子,该起来了!吃完饭上工了!"父亲粗犷的声音穿透门板。
孙玄迷迷糊糊地抬起手腕,手表的指针刚好指向四点整。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只有几声零星的鸡鸣预示着黎明将至。
他苦笑着揉了揉酸痛的腰——昨天割了一整天麦子,手掌上的水泡还没消呢。
"还有两天..."孙玄小声嘀咕着,却还是利索地套上衣服。秋收不等人,熟透的麦子多耽搁一天就可能掉粒。
堂屋里,煤油灯投下昏黄的光晕,孙母正在往篮子里装玉米面饼和咸菜疙瘩,孙父已经穿戴整齐坐在桌前。
孙逸顶着乱蓬蓬的头发走进来,兄弟俩对视一眼,同时露出无奈的苦笑。
"快吃,趁热。"孙母端上一盆冒着热气的玉米粥,"今儿个割东洼地,听说公社书记要来检查。"
简单的早饭在沉默中结束,孙父抹了把嘴,把镰刀别在腰间:"走吧,趁着凉快多干点。"
推开院门,孙玄惊讶地发现村里已经热闹起来。各家各户的煤油灯陆续点亮,像散落在黑夜里的星星。
远处打谷场上,早有人影在晃动——那是值夜的人正在翻动麦垛,防止潮湿发霉。
"孙大叔!"一个瘦小的身影从黑暗中跑来,是记分员孙瘸子的儿子孙小柱,"队长让我通知,今天知青也来帮忙!"
孙父点点头:"城里娃娃能干啥?别添乱就不错了。"
东洼地头,大队长孙永年正在分配任务。十几个穿着整齐却动作生疏的年轻人站在一旁,在满是补丁的农民中间格外扎眼。
孙玄认出那是今年刚分到村里的知青,最小的看着才十六七岁。
"同志们!"大队长站在拖拉机上,声音洪亮,"今天咱们要拿下东洼地!老把式带知青,一人盯一个,可不能糟蹋粮食!"
孙玄被分到一个戴眼镜的男知青,白白净净的,自我介绍叫周卫国,来自沪上。
"孙、孙同志,"周卫国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这个怎么用?"他拿着镰刀的样子像握钢笔。
孙玄忍住笑,手把手教他摆姿势:"手腕别太僵,顺着麦秆的劲儿走..."
晨光微熹时,劳动正式开始。老农们弯下腰,镰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四合院:重回50年,傻柱从军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嘎子剑)的经典小说:《四合院:重回50年,傻柱从军》最新章节...
- 2306992字11-15
- 风流村医自由的沃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林小仙)的经典小说:《风流村医自由的沃土》最新章节全文阅...
- 4928449字05-20
- 阴鬼老婆之梦境特工养成记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墨泽玄坛)的经典小说:《阴鬼老婆之梦境特工养成记》最新章...
- 1028964字12-14
- 都市全能神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晨烁)的经典小说:《都市全能神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1878742字11-16
- 透视不赌石,你又在乱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迟暮流年)的经典小说:《透视不赌石,你又在乱看》最新章节全...
- 4147110字04-17
- 你透视眼不去赌石,乱看什么呢!
- 【小人物逆袭+透视+赌石+鉴宝+捡漏+神豪】秦朝阳,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社会晃荡两年...
- 3795767字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