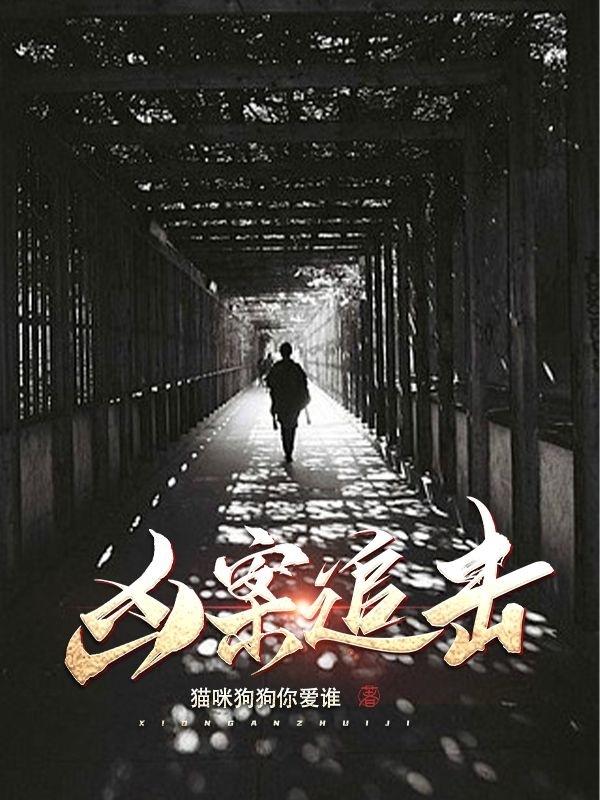第13页
听见动静,西装男抬眸看过去。
“妈。”谢秋应了一声,“我们回来了。”
方鸿应道:“是,夫人。”
谢秋:“……”
只可惜,方特助不久后也会倒向贺二少的阵营。
他先回自己的房间,好好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睡衣,这才推开隔壁的门。
病床上的男人双眸闭阖,像是在做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梦。
他干脆将沉睡中的男人当做树洞,开始碎碎念起来:“说实话,其实我长得也还行吧,一直都是被别人追着跑的,没想到这次……唉,希望贺二少能早点明白,我对他没有丝毫非分之想,可以对我nice一点。”
他隻想安安分分地过完两年半,然后远离这些豪门恩怨。
很快,他端着脸盆回到病床前,准备给贺司宴擦身体。
但是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主动去解一个成年男人的衣服,指尖不由抖了抖。
他的注意力都在扣子上,没发现贺司宴的眉心极轻地蹙了一下。
然而他显然低估了男人的体重,不仅没将男人的上半身抬起来,反而差点跌倒。
但他低着头,潮湿微卷的发丝在男人不甚明显的腹肌上来回蹭了蹭,
“对不起对不起……”谢秋连忙抬起头,诚恳地道歉,“是我太高估自己了。”
昨天那个护工做起来很轻松的样子,果然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
虽然知道男人没有知觉,但他的动作依旧很轻,温柔细致地擦过每一寸皮肤。
手感挺好的,就是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反正肯定坚持不到醒来的那天。
擦干净上半身后,他眼睛半睁半闭,双手放在男人的胯部,狠了狠心,一把将睡裤褪了下去。
那里是腿上最敏感的地方,似有若无地蹭在腿侧的指腹比毛巾更温热柔软。
“不好意思,头髮没擦干。”他条件反射地伸出另一隻手,擦了擦水珠氤开的部位。
谢秋呆了几秒,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干了什么,耳根霎时变得滚烫。
谢秋目瞪口呆,好半晌后才结结巴巴地唤道:“贺、贺先生?你醒了吗?”
谢秋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打开搜索框输入问题。
原来勃-起也是植物人的正常生理性活动之一,是无意识的行为,不能代表病人已经苏醒或者恢復意识。
谢秋继续往下滑,随手点进相关问题的链接,突然间瞳孔微震。
谢秋:“……”
不对,就算他能生孩子,可他跟贺司宴是假结婚,两人只是名义上的夫夫而已,他为什么要考虑这种事情?
相关小说
- 斩妖灭鬼,从高中开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雪里黑)的经典小说:《斩妖灭鬼,从高中开始》最新章节全文...
- 593612字07-30
- 我女友是侦探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萧梨花)的经典小说:《我女友是侦探》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1101913字07-28
- 凶案追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猫咪狗狗你爱谁)的经典小说:《凶案追击》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177476字07-30
- 劫天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浮梦流年)的经典小说:《劫天运》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24301574字07-29
- 规则怪谈,原来我才是BOSS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软毛小肥龙)的经典小说:《规则怪谈,原来我才是BOSS》最新章...
- 430742字07-30
- 是谁害死了猫
- 294302字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