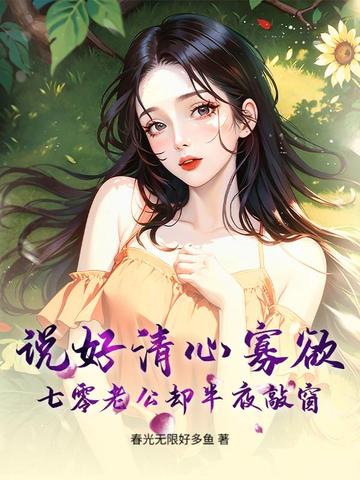第275章 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
的几个字》,因此,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现在,两人都是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参与古文字成立大会,关系也逐渐熟络,之前还互相讨论各自的文章,因此苏亦比在场的众人还提前知道他的文章内容。
李家浩是小辈。
学术报告安排的时间比较靠后。
苏亦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释,不是很感兴趣。这玩意他太考究功底了,他就是半桶水,对上李家浩,他也只有听的份。
相比较裘锡圭跟李家浩这对师生,朱德熙先生在战国文字方面的研究造诣更深,因此,他的文章《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也是专攻这个方向。
除了玺印、陶文,楚简、楚帛书、汉竹简、盟书和铜器铭文等方向,朱德熙先生都有涉略。
后来,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还合着《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算是北大中文系古文字方面主要学术的成果之一。
相比较中文系,考古专业这边就低调了很多,也不对,应该说更加接地气一点,比如高铭先生的文章《侯马载书盟主考》。
先不说别的,仅仅从这篇文章的名字,苏亦就能够分析出好多学术八卦。
一般来说,学界提及侯马出土的文书都会用“侯马盟书”来形容。
因为1965年侯马盟书出土的时候,文物局谢辰生先生专程赶去侯马视察,并带部分盟书标本回京,给郭沫若先生鉴定。隔年,郭沫若就写《侯马盟书试探》一文。侯马盟书由此名扬海内外。
在郭沫若先生之前,是没有这个称呼的。
比如侯马考古队队长张晗先生在写关于这批文书的时候,也是《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这个标题。跟郭老的《侯马盟书试探》同时刊发在当月的《文物》。
《文物》月刊发出消息之后,第一位加入侯马盟书讨论的就是陈梦家先生。
他1966 年《考古》5 期发表了《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
唐兰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关系有点微妙,很多学术上的观点是不认可的。
因此,他在72年他在《文物》上写了一篇文章《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也没有用“侯马盟书”而是直接沿用陈梦家的“载书”。
这篇文章,唐兰先生提出四个问题:
一、主盟的人是谁;
二、这次盟誓为的什么;
三、在什么时候;
<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14页
相关小说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都市逍遥小神医
- 都市逍遥小神医是由作者花小楼著,免费提供都市逍遥小神医最新清爽干净的文字章节在...
- 726505字12-21
- 说好清心寡欲,七零老公却半夜敲窗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春光无限好多鱼)的经典小说:《说好清心寡欲,七零老公却半夜...
- 426903字07-13
- 贷款武道,校花表姐酸死了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曹家孟德)的经典小说:《贷款武道,校花表姐酸死了》最新章节...
- 474873字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