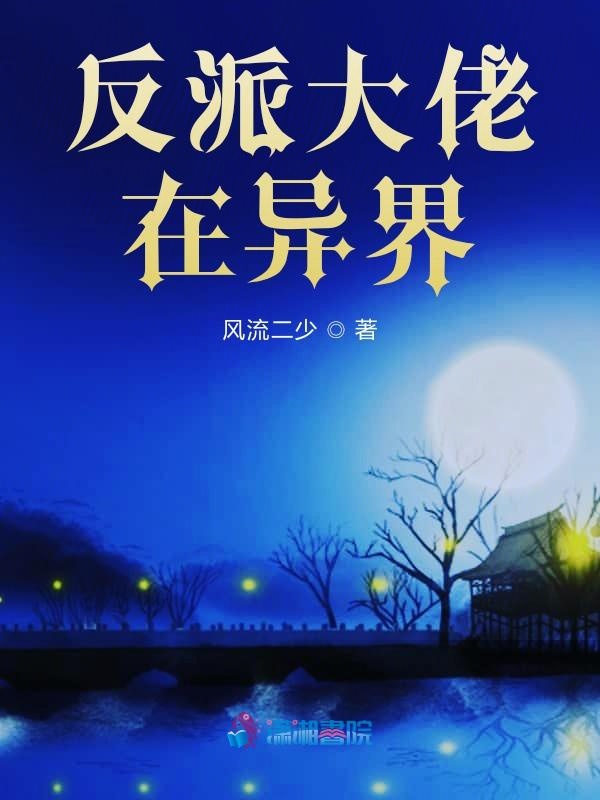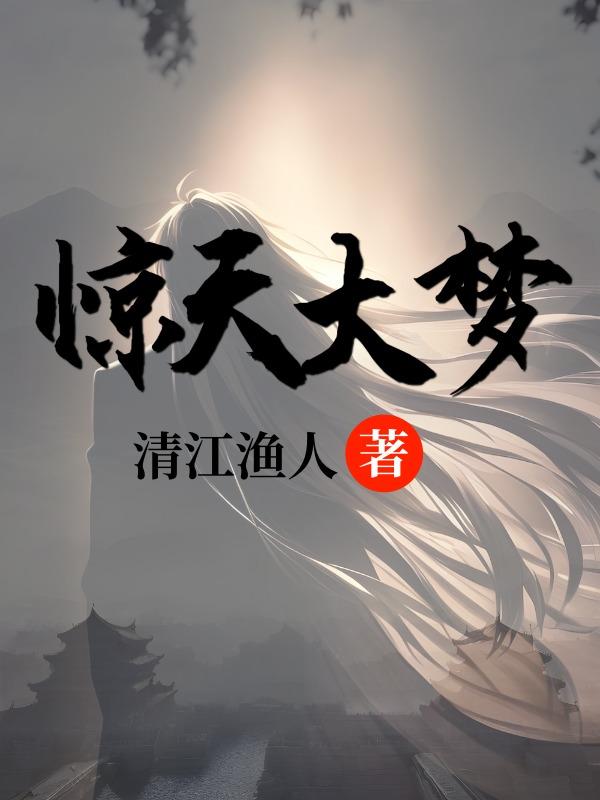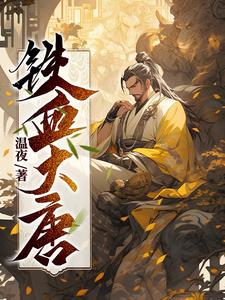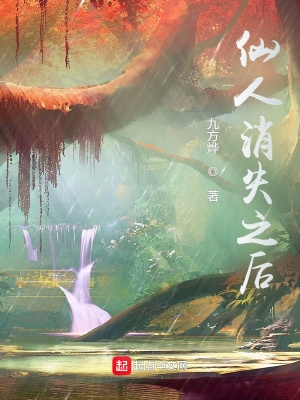第229章 徐氏
> 她知道这不是求娶,是结盟。
庐江徐家是本地望族,父亲手握兵权,孙策要在江东站稳脚跟,需得这样的助力。
而她,就是那枚最恰当的棋子。
“愿听父亲与将军安排。”她答得干脆,没有丝毫扭捏。
建安五年,徐氏嫁入吴郡。
婚礼那日,江风卷着红绸掠过城门楼,她坐在花轿里,听着外面百姓的欢呼,忽然想起舒县后院的那棵枇杷树。
如今该挂满黄澄澄的果子了吧。
孙权那时还不是后来的吴大帝,只是个眉眼尚带青涩的少年将军。
他初见徐氏时,总被她那双过于沉静的眼睛看得不自在。
新婚之夜,红烛摇曳,他举杯道:“你若不愿……”
“夫君不必多言。”徐氏接过酒杯,与他轻轻一碰,“既入孙门,自当尽妇道,分君忧。”
她仰头饮尽杯中酒,酒液辛辣,却让她想起父亲教她看地图时说的话:“天下棋局,落子便不能悔。”
婚后的日子,比徐氏预想的要平静。
孙权常在外征战,她便在府中打理家事,闲暇时研读他留在案头的奏章。
有次孙权回府,见她在批注一份关于盐铁专营的文书,字迹遒劲,竟有几分其父徐琨的风骨。“你也懂这些?”他有些惊讶。
“幼时听父亲与幕僚谈论,记下些皮毛。”徐氏指着其中一句,“海盐产区若由官府直接管理,虽能增收,却恐失民心。不如仿蜀地之法,官民共营,三七分成,既保了税利,又安了商户。”
孙权盯着她看了半晌,忽然笑了:“原来我娶的不是个夫人,是个谋士。”
建安十三年,赤壁战火起。
孙权在柴桑召集群臣议事,张昭等人力主降曹,周瑜与鲁肃则劝战。
争论最激烈时,徐氏正在后堂为将士缝制寒衣,听着前堂传来的争执声,她让青禾取来笔墨,写了张字条递给孙权的近侍:“曹操虽强,然北人不习水战,且荆州新附,民心未稳。周郎有赤壁之险可依,鲁肃掌粮道无忧,此战当战。”
孙权见了字条,忽然拍案而起:“孤意已决,与曹贼一战!”
后来赤壁大胜,他回府对徐氏道:“那日若无你字条,孤或许真要被张公等人说动了。”
徐氏正在灯下为他缝补战袍,闻言只是淡淡一笑:“是夫君自有决断,我不过是恰逢其会。”
她心里清楚,孙权需要的不是一个指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10页
相关小说
- 反派大佬在异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风流二少)的经典小说:《反派大佬在异界》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1729852字03-12
- 炼金术士手册
- 炼金术士手册章节目录,提供炼金术士手册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773159字04-10
- 兽人之附能师
- 96592字05-03
- 惊天大梦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清江渔人)的经典小说:《惊天大梦》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445817字12-26
- 大唐第一亲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温夜)的经典小说:《大唐第一亲王!》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3179746字09-20
- 仙人消失之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九方烨)的经典小说:《仙人消失之后》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7648466字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