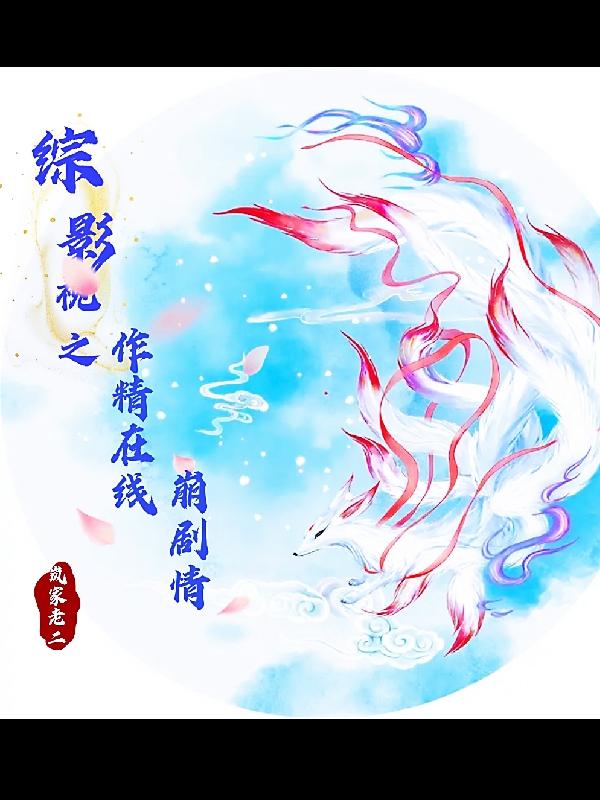治病(微h) jiz ai 17 .c om
又开始蔓延。
她按着他的身体,从锁骨摸到胸前。手心擦过乳环,他的脖子紧绷出苍白与红交织的线条。他反手握住她的手腕,带着她继续往下。
他说:“你去吃点东西。是不是还没吃晚饭?”
她问:“你呢?”
她看着他被毯子遮挡的下半身偷笑,他面无表情地盯着她走去岛台吃饭,在她吃东西时一直看着,仿佛这样可以治病。她吃饭间隙跟他聊天,说起了最近的工作。
他懒洋洋地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但也是他们不长眼睛。除非他们做了像你爸那样的事,谁值得你费心思搞垮?”
吃完饭又过了一会,z还接着工作,晚了就被他催去休息。第二天z还有事要回去,这次来着实是赶行程。她站在他床前踌躇。
“行吧,”她撇嘴,“好好睡吧少爷。”
他眯着眼睛看,黑暗中看见她披着头发,轻手轻脚地走到他床前,摸他的额头,似乎想给他换降温贴。
她吓了一跳:“你醒着怎么不说话?”
“你想干什么?”他问。
他在黑夜里注视着她,似乎想从中描摹出她的模样。
她呼吸软了几分,本来没什么事该走了,可脚生了根似的。看不到彼此全貌的困顿里,似乎更容易滋生痴态,她定定站着,又俯身将脸贴在他枕边。
“别想走了。”他说。
衣服摩擦和喘息声,像原始人磕碰。他扯下她的内裤,又褪下
高潮和哭声同时爆发,闷在怀里的啜泣,他引着她找到胸前新增的,代表她所属物的标记,疼痛感使他敞开归属。不安的,嫉妒的恐惧,终于爆发,无法一下根除,所以只能发泄。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半睁着眼睛。有人坐在床边,伸进被子找到她的手。她顺着抓住,嘟囔着说要走了。
他似乎笑了笑,手上传来的体温显示烧已经退了,看样子心情不错。他弯下腰半抱着她,低头亲她的眼皮。
他抱了一会,难舍难分的样子,又笑着说:“多亏了你……让我病好了。”——
以前嘴硬现在补偿性sweet talk,一半因为他觉得亏欠,另一半是这个颠公真的喜欢说。
相关小说
- 徒儿,下山去祸害你师姐吧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殇殇)的经典小说:《徒儿,下山去祸害你师姐吧》最新章节全...
- 9910530字07-30
- 震惊杀手榜,大佬竟是华国大学生
- 震惊杀手榜,大佬竟是华国大学生是由作者土豆茄子一起吃著,免费提供震惊杀手榜,大佬...
- 3352008字07-30
- 我的一九八五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解剖老师)的经典小说:《我的一九八五》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4559791字07-30
- 神奇宝贝:系统开局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星辰海浪)的经典小说:《神奇宝贝:系统开局》最新章节全文...
- 4003158字07-30
- 快穿世界吃瓜第一线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琪琪家的猫)的经典小说:《快穿世界吃瓜第一线》最新章节全...
- 5956567字07-30
- 综影视之作精在线崩剧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岚家老二)的经典小说:《综影视之作精在线崩剧情》最新章节...
- 2392369字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