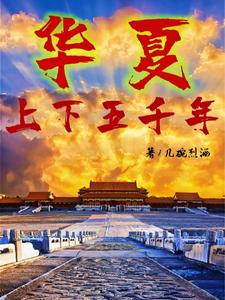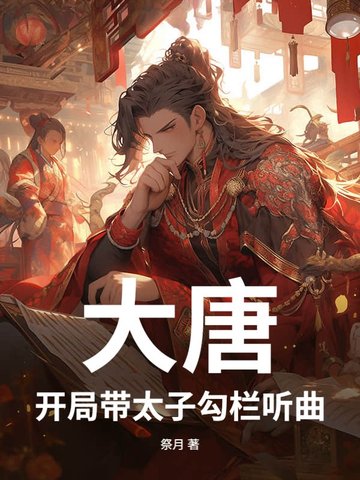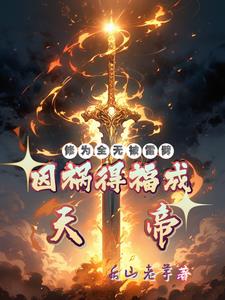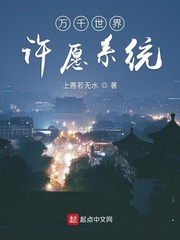第一百七十五章 无标题(中)
..这应该是他早就计划好的选择!......连他最得意的合唱手笔都被尘封,毅然以无标题的纯器乐作为最后一击,试图向着当年本格主义时代的‘掌炬者’登顶过程寻求某种同一性、甚至是超越性......极其狂妄、极其危险、不留余地的野心!......”
在场的乐评家与各界听众,在音乐发展至如此精彩的境地时,无不动容!
或者,这里可用一种更危险的描述方式。
范宁这次不是拒绝了“用标题写音乐”,而是将其关系反转了过来,“用音乐产生标题”!
“没有哪一音乐有如此抽象,又没有哪一音乐有如此具体!......因为,无论是他的曲式结构中那种无规律、无目的循环,还是指挥手法中所表现的一泄千里、不可遏制的感情,以及各种动机、意绪、连绵不断的永恒进行,都是艺术家对他所生存的那个世界的描述!......”
他成功了。
至少从开篇来看,他的确成功了。
每个听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灵性,创造自己的标题,去归纳其中任何引起自己触动的东西!
这里的一切自始至终,处于压抑的、难以排遣的悲哀气氛中。
铜管组的乐手们一路以来,似乎做了不少积极的抗争,却在最后的时刻彻底失去力量。
尾奏,三连音送葬动机重现。
乐队很快陷入死寂,加了弱音器的管乐号角之声,在时空中渐行渐远。
仅仅作为空谷回声的独奏长笛,以极轻的力度吹出最后的分解#c小三和弦。
“咚。”一声沉闷的低音提琴拨弦作结。
仿佛很有预见性。
这个第一乐章的气氛,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如今的现实”还要略胜一筹。
接下来是否会有喘息之机?
听众们如此猜测,但就在此时,他们看到范宁手腕猛然翻折,像折断一根枯枝。
低音弦乐手的琴弓同时离弦提起。
那是暴风雨来临前,云层与大地之间绷紧的寂静。
下一刻,a小调的狂暴序奏倏然劈裂而出,如同闪电贯穿阴云!
第二乐章,“如暴风雨般激烈,并更加激烈”!
低音弦乐器发出痛苦的嘶叫,铜管与打击乐以癫狂愤怒的姿态竞相回应!
听众们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之前第一乐章的曲式其实“很有问题”,通篇下来去看,只是一个“死亡的引子”!<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华夏:上下五千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几碗烈酒)的经典小说:《华夏:上下五千年》最新章节全文阅...
- 806557字11-19
- 九玄焚天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异瞳癌)的经典小说:《九玄焚天》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1021981字06-27
- 大唐:开局带太子勾栏听曲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祭月)的经典小说:《大唐:开局带太子勾栏听曲》最新章节全...
- 427775字07-04
- 肉身证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后山老芋)的经典小说:《肉身证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611806字11-11
- 万千世界许愿系统
- 万千世界许愿系统章节目录,提供万千世界许愿系统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9663819字07-03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811279字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