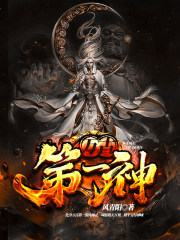第532章 自是春江秋月明(五)
在廊下晒太阳——原来看着年轻人奔跑的样子,真的会让人忘记鬓边的霜雪。
腊月初八,温北君周年祭。梅林里的雪还未化尽,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最粗的那株梅树下。
"卫将军。"徐荣转过身来,肩上落满花瓣。这个被称作"杀绝将军"的男人,直到今日才出现在我面前。
如果回到过去,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天天在大梁学宫昼寝的学子,那个曾经面黄肌瘦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如今却勇冠大魏三军。先生带过的所有小辈中,肖姚战死,左梁战死,无论是吴泽还是吴怀,刘棠还是郭孝儒,甚至包括先生的侄女温鸢和女儿温瑾潼都不是冲锋陷阵的猛将。只有眼前的徐荣继承了温北君的勇武,凡对阵必冲锋在前。
"北狄有异动。"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下意识去摸腰间的玉佩——那是先生留给我的。玉佩上的"长恨"二字已经磨得发亮。
徐荣的目光落在我手上,突然笑了:"他现在肯定在骂娘。"
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徐荣的眼泪砸在刀鞘上,溅起细小的水花。他抬手抹了把脸,粗声道:"那老狐狸,连自己的死都算进去了。"
承平七年冬,吴泽抱着刚满月的儿子来找我。小娃娃裹在虎皮襁褓里,睡得正香。
"请将军赐名。"吴泽恭敬地说。
我看着这个在襁褓中酣睡的婴孩,想起先生当年为我讲解《诗经》时的情景。"叫念平吧。"我说。
吴泽怔了怔,突然跪下重重磕了个头。我知道他听懂了——念平,念北,都是先生取名的习惯。
"平安长大就好。"我轻声说,不知是在对谁说。
夜深人静时,我常去藏书阁。案几上永远摊开着先生批注到一半的《六韬》,朱砂笔搁在砚台边,仿佛主人只是暂离。
这夜,我正批阅军报,忽听门轴转动的声音。回头望去,只见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一道斜斜的光痕,像极了某人倚门而立的身影。
"先生?"我下意识唤道。
无人应答。只有案头的《六韬》被风吹动,停在第七十六页。那是先生批注的最后一页,朱砂小楷写着: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然百姓安乐,方为真太平。"
落款处的墨迹有些晕开,仿佛曾被水渍浸染。我总疑心那是先生的泪,却又觉得,他那样的人,怎么会哭呢?
我几乎没有见过先生的眼泪,我很想看到史书上会如何评价我的先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
相关小说
- 炼神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秋月梧桐)的经典小说:《炼神鼎》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3735515字07-30
- 万古第一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风青阳)的经典小说:《万古第一神》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20326374字07-30
- 修罗剑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三寸寒芒)的经典小说:《修罗剑神》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10081387字07-30
- 乾坤塔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新闻工作者)的经典小说:《乾坤塔》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5196247字07-30
- 天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沐潇三生)的经典小说:《天渊》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更...
- 5828554字07-20
- 大唐混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可乐变汽水)的经典小说:《大唐混子》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94936字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