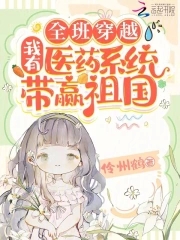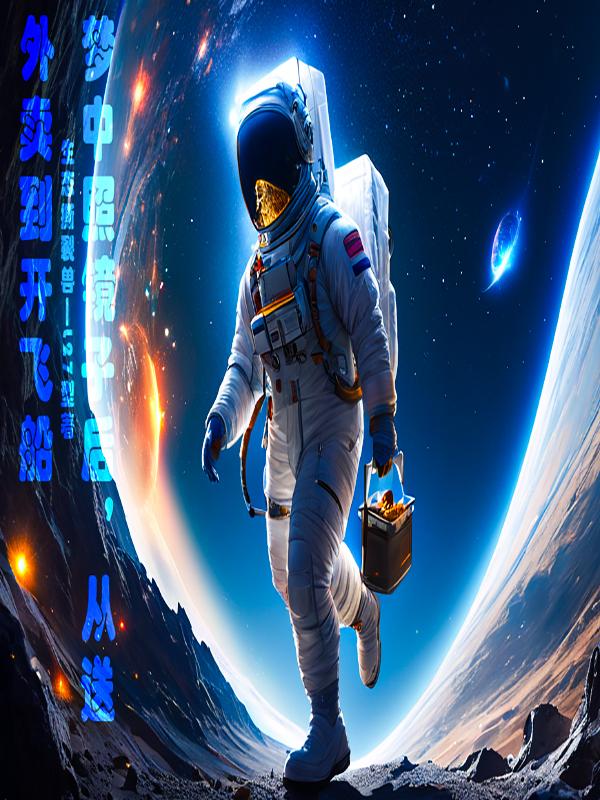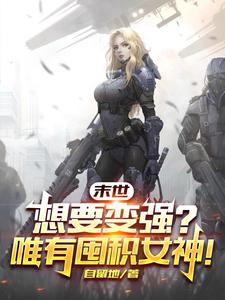第49章 射礼中的君子之道:儒家竞技伦理的文明省思
洞书院的 “射圃” 中具象化:书院生徒需定期习射,每次射前需朗诵《射义》章节,射后集体讨论 “中与不中” 的道德寓意,使射礼成为 “存天理,灭人欲” 的修养手段。
明代王阳明进一步将射礼与 “心学” 结合,提出 “射以观德,德本于心”。他在南赣剿匪期间,曾组织军民举行乡射礼,以 “正心”“睦邻” 为宗旨,将军事训练与道德教化结合,写下《南赣乡射礼》一文,详细规定 “每岁孟冬,太守集士民于射圃,行三揖三让之礼,然后射”,开创了 “以礼治军” 的实践范式。
(三)清代:世俗化的竞技转型
清代 “骑射” 作为满洲 “根本”,在保留军事功能的同时,进一步向世俗娱乐渗透。北京的 “善扑营” 本为宫廷摔跤机构,却衍生出民间 “射虎社” 等竞技团体,其成员 “衣短后之衣,执竹弓木矢,以射为戏”,将射礼转化为市井娱乐。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贾宝玉与薛蟠等人 “在院内射鹄子取乐”,射礼已从贵族礼仪变为富家公子的消遣,折射出传统竞技伦理的世俗化转型。
(四)辽金元:骑射文化的双向融合
辽代契丹族的 “瑟瑟仪” 将射柳与祈雨结合,皇帝 “射柳者以毡帽接地,得柳者欢呼,不得者以冠履罚之”,既保留草原民族的竞技传统,又吸纳汉族礼仪元素。元代 “贵由赤”(长跑比赛)与射礼并行,其 “起自上都,至大都,越三时而后至” 的规则,体现了蒙古帝国对多元竞技文化的包容,这种 “各美其美” 的竞技观,暗合孔子 “和而不同” 的哲学。
(五)明清天主教文献中的射礼书写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详细记录了明代乡射礼的场景:“士大夫执弓而立,进退周旋必中礼,其容肃,其气沉,观者皆叹服”。他将射礼与欧洲骑士精神对比,认为 “中国之射,重德甚于重技,与基督教‘荣誉即美德’有相通之处”。这种跨文化书写,为射礼伦理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早期样本。
四、现代性冲击下的竞技伦理:从 “礼争” 到 “力争” 的范式转换
工业文明的兴起,使竞技精神发生根本性转向。当奥林匹克五环取代青铜箭靶,当兴奋剂检测替代 “揖让之礼”,孔子的竞技哲学在现代性浪潮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竞技的祛礼化与工具化
现代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使 “争” 的本质从 “德胜” 异化为 “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全班穿越,我有医药系统带赢祖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伶州鹤)的经典小说:《全班穿越,我有医药系统带赢祖国》最新...
- 342058字10-21
- 泅水(人鬼骨科)
- 泅水(人鬼骨科)章节目录,提供泅水(人鬼骨科)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127326字06-23
- 求生:魔法灾变世界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沐水沧澜)的经典小说:《求生:魔法灾变世界》最新章节全文...
- 1323949字11-23
- 末世:我穿梭两界成霸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小孩骑单车)的经典小说:《末世:我穿梭两界成霸主》最新章...
- 1068137字12-19
- 梦中照镜子后,从送外卖到开飞船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生态撕裂兽l-27型)的经典小说:《梦中照镜子后,从送外卖到开...
- 1635001字10-28
- 末世:想要变强?唯有囤积女神!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自留地)的经典小说:《末世:想要变强?唯有囤积女神!》最...
- 1802131字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