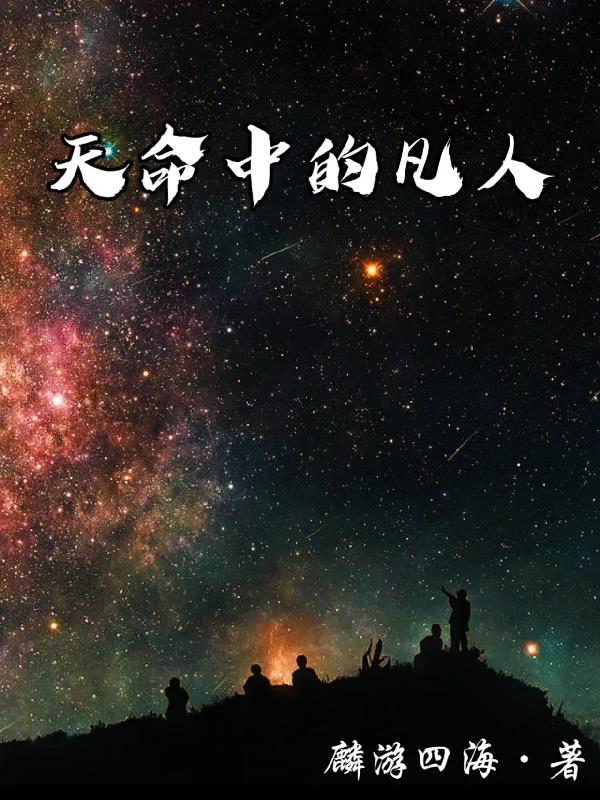第一千一百五十五章 此策非法,此税不公!
,仿佛又敲起了三月策试时的节奏。
朱瀚立于屋檐下,望着满庭雨脚,一动不动,手中却握着一卷未拆的策帖。
“是杜和送来的。”
沈镇将一盏温茶递来,低声禀报,“说是青策堂内新招一少年,自号‘策狂’,言语肆意,众士子颇为推崇。”
“策狂?”朱瀚挑眉,嘴角含笑,“年少,狂得起来才好。”
“可他说——策不可藏。”
沈镇声音微顿,“意指王爷之‘策隐所’,并非正道。”
朱瀚不怒反笑:“那他倒是讲得好。说策不可藏,那便看他能不能讲得响。”
他拆开那卷策帖,纸墨未干,果然如其人,字如走马,文锋直逼: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藏策者,疑人;散策者,信众。策不为藏,藏则策亡。王侯策士,若藏而自居高位,岂不与帝王之术相类,非真士之道。”
朱瀚看罢,缓缓将策帖合上,丢于桌案:“去,把杜和叫来。”
沈镇一愣:“王爷是……要?”
“是时候放他出去走走。”
朱瀚语调平静,“他在青策堂讲得久了,难免忘了,策不是讲给士子听的,是讲给这个天下听的。”
“让他带着这个‘策狂’,下郡走一遭。就说是我命他巡访民意。若能讲动一镇之民,孤便承他一句‘策不可藏’。”
沈镇领命,欲退。
朱瀚忽又道:“且慢。”
他取笔写下三字,封于一方信封中:“这封信,交给那‘策狂’本人。切勿让旁人知晓。”
沈镇接过,微见疑色,却未多问。
十日之后,东郊文山县外,连夜小镇,一家客栈门口,挂着破布旗,上书:“策评三席”。
杜和坐于堂中,着布衣,眼神冷静而寡言。
对面立着一少年,衣衫褴褛,腰间却悬一卷竹简,自号“策狂”。
“你说策不可藏。”杜和道,“可你讲策不过三日,便惹来镇民围观,一日之中数起争执,坊中书院两度停课,教谕亲来劝止。”
“我讲策,讲的是醒人之言。”
少年眼神明亮,“他们争,是因为醒了。若策不能惹人动心,便只是纸上文章。”
“可你叫他们去问县令,为何不准市集外摆摊?”
“我叫他们问的是‘为何不能摆’,不是‘为何不能服’。”
少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6页
相关小说
- 大明:如此贪的駙马,朕杀不得?
- 3593287字07-30
- 帝国崛起:我为大明续命七百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住在南极的小鲨)的经典小说:《帝国崛起:我为大明续命七百...
- 4958086字06-27
- 仙子,一日得道了解一下
- 4438255字07-24
- 超级系统杀怪爆装升级
- 1125325字07-19
- 天命中的凡人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麟游四海)的经典小说:《天命中的凡人》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445145字07-19
- 九玄邪尊
- 11331894字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