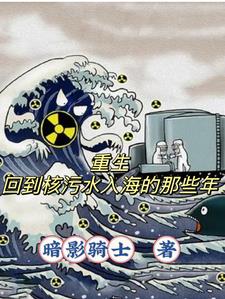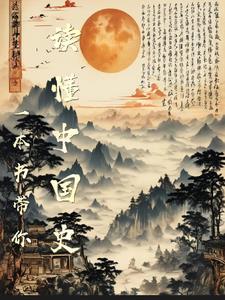第2章 蒙元史话 第一节:成吉思汗崛起:纵横草原,一统蒙古
。
外部压迫:金国的“减丁”与草原的“工具化”
草原的混乱,因南方金国的干预更趋恶化。金国灭辽后,为巩固北方边疆,推行“减丁”政策:每三年派军队进入草原,以“普查户口”为名屠杀青壮牧民,《金史·完颜襄传》载:“(大定)二十五年,北边大饥,诏免租税,发仓廪赈之。襄请曰:‘蒙古诸部,种类滋繁,恐数为边患,宜择其豪首,量加存抚,其余分散,各安其业。’上从之。”所谓“存抚”,实则是通过扶持弱小部落(如塔塔尔部)制衡强大部落(如乞颜部),使草原永远处于“分裂状态”。
更残酷的是,金国将草原视为“牧马场”与“兵源地”。据《黑鞑事略》记载,金军“每岁秋,遣将率兵巡边,遇蒙古人畜,辄尽杀之,谓之‘打草谷’”。这种系统性掠夺,使草原经济濒临崩溃——牧民失去马匹(游牧民族的“第二生命”),无法迁徙避灾;牛羊被抢,只能靠采集野果、捕猎旱獭为生。《蒙古秘史》中诃额仑夫人带铁木真兄弟“吃野果、挖草根”的记载,正是当时底层牧民生存状态的缩影。
时代之问:谁能为草原“立规矩”?
草原需要的不是更强大的部落,而是一位能打破“血缘壁垒”“终结血仇”的领袖。《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指出:“当草原陷入混乱时,人们渴望一位‘能以剑止戈、以法代仇’的统治者。”这种渴望,本质是对“秩序”的需求——经济上需要稳定的游牧空间,政治上需要统一的决策机制,文化上需要共同的认同符号。
此时,铁木真已从斡难河边的弃儿成长为乞颜部残余势力的核心。他的优势在于:其一,童年磨难使他深谙“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却未陷入“以暴易暴”的循环;其二,早年经历(如联姻、复仇)让他学会“利用矛盾”——既联合弘吉剌部获取外戚支持,又借克烈部王罕的兵力对抗仇敌;其三,他提出了超越部落的愿景:“我们要建立一个‘共饮班朱尼河水’的共同体,不再为争夺草场互相残杀。”这种愿景,恰好回应了草原各部对“秩序”的渴望。
二、孤狼成长:从弃儿到乞颜部“共主”的蛰伏
童年淬炼:命运的“生存课”
1162年铁木真出生时,也速该刚击败塔塔尔部首领铁木真兀格,因此为儿子取名“铁木真”(意为“铁匠”,象征坚韧)。但命运残酷:9岁时,也速该带他到弘吉剌部定亲,返回途中被塔塔尔人毒杀。部落贵族见乞颜部失去领袖,纷纷携部众离去,连也速该的部下“豁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8页
相关小说
- 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暗影骑士)的经典小说:《重生:我回到核污水入海的那些年》...
- 522322字09-17
- 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凝香笔)的经典小说:《一本书带你读懂中国史》最新章节全文...
- 1821613字06-26
- 崩坏原神铁道:开局曝光三大主角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银河小完能)的经典小说:《崩坏原神铁道:开局曝光三大主角...
- 1386593字07-14
- 末日无限副本,这一枪你可能会死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最映刻)的经典小说:《末日无限副本,这一枪你可能会死》最新...
- 3325982字06-20
- 核战废土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用户20675163)的经典小说:《核战废土》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1448501字11-19
- 穿书师尊是个大反派
- 2926577字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