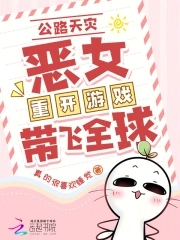第二十六章 南宋抗金烽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城三日,彼自乱矣。”最终,宗弼“拔营北去,自是不敢复窥淮东”(《宋史·刘锜传》)。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顺昌之战被称为“南渡以来,援淮第一”(《读史方舆纪要》),其意义不仅在于守住淮南,更在于证明了南宋军队“以智御力”的可能性——即使兵力处于劣势,仍可通过战术创新扭转战局。
柘皋之战(1141):张俊、杨沂中的“联合作战”
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金军分路南侵,张俊、杨沂中、刘锜三路宋军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会战。此战是南宋对金作战规模最大的一次胜利:张俊率“踏白军”(精锐骑兵)正面突击,杨沂中以“长枪手”破金军骑兵,刘锜则“以步兵持长斧破其拐子马”。史载:“金人大溃,退至店埠河,溺死者不可胜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柘皋之捷后,南宋朝廷却急于求和。赵构担心“诸将权重”,密令秦桧“趣班师”。岳飞接到“措置班师”的诏令时,正在朱仙镇与义军联络,悲愤道:“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宋史·岳飞传》)
三、江湖与庙堂:抗金背后的民意与博弈
1.底层民众的抗争:“人民战争”的雏形
南宋抗金的胜利,离不开底层民众的支持。《宋史·忠义传》记载,仅河北地区就有“义兵首领”百余人,“皆率乡里子弟,保聚山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八字军”:王彦率部在太行山“筑寨自保”,“每战则披发,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队伍发展到十万余人,“金人患之,悬赏购其首”。
南方百姓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抗金:江西“义社”组织“乡兵”,“农隙则教战,有事则荷戈”;福建“海舟”商人“私运粮饷”至襄阳,“冒死渡江”;甚至连女性都加入抗金行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康(今南京)妇女“结寨自保,贼至则登陴拒守,贼退则负粮以济官军”。
这种“全民抗金”的局面,本质上是“华夷之辨”与“保家卫国”的双重驱动。正如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金军的屠刀砍向每一个家庭时,反抗不再是军人的专利,而是全体民众的本能。
2.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南宋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的斗争贯穿始终。主战派以李纲、宗泽、岳飞为代表,主张“雪靖康之耻”,恢复中原;主和派以赵构、秦桧为代表,主张“偏安求存”,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5页 / 共7页
相关小说
- 智械之后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夏玉月)的经典小说:《智械之后》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站...
- 830855字10-28
- 译电者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青灯轻剑斩黄泉)的经典小说:《译电者》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2328375字07-26
- 全民公路求生:欧皇重开带飞全球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真的很喜欢睡觉)的经典小说:《全民公路求生:欧皇重开带飞...
- 693959字07-30
- 归墟
- 42957字06-28
- 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UG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白凤今天不想码字)的经典小说:《开局一辆购物车发育全靠卡B...
- 994528字10-01
- 黑暗本源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番石榴爵)的经典小说:《黑暗本源》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485452字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