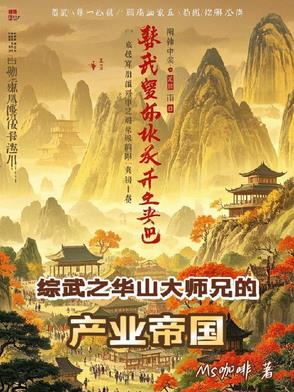第264章
“我以前看过类似的论文,在一部分学者眼里,调换儿本质是对抱错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或者对孩子被有心人给调包的恐惧而衍生而来……”布鲁斯说。
“那班聂调包后的山杨木,听上去像产后抑郁症或者孩童夭折后,母亲因为过度伤心而得的癔症。”克拉克说。
“话虽如此,不过在这里,魔鬼和精怪是实打实的,二位,现在不是搞社会分析的时候。”戴安娜说。
事实上,也有一些说法,若是接受过基督的洗礼,就不会被带走——不过这条先不管在他地是否奏效,在俄罗斯明显行不通。对此,布鲁斯的第一反应和布莱雷利一样:不愧是拥有圣愚文化的国度。
接受即存在,在这个异教与基督并行这件事,对于俄罗斯人来讲并不冲突。
“尽管也是换生灵,他的情况则更复杂一点——”
……
……
在苏尔把干草垛铺好后,有人敲了敲那块破门板。
他抬起头,发现布莱雷利正站在门口,而夔娥正躲在他身后,弯着腰,小声地“嗨”了一声。
“你们怎么……”
“您不欢迎?哦确实,毕竟您先来的,难道还要我给您说点别的好话才能进来?”布莱雷利一摊手,似笑非笑,语气讥讽。夔娥在他身后努力地比划,意思是他猫病犯了不用理他。有时候,这人一准备阴阳怪气些什么,就老爱用敬词来刺人的毛病绝了,也就苏尔脾气还不错,换她早就用物理手段让他闭嘴了。
一阵拉扯过后,他们决定一起躺干草垛——也许在谢苗大叔眼里,他们三个活像有病一样,放着有屋顶的教堂不呆,非要来挤破柴房。
对于夔娥和苏尔来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