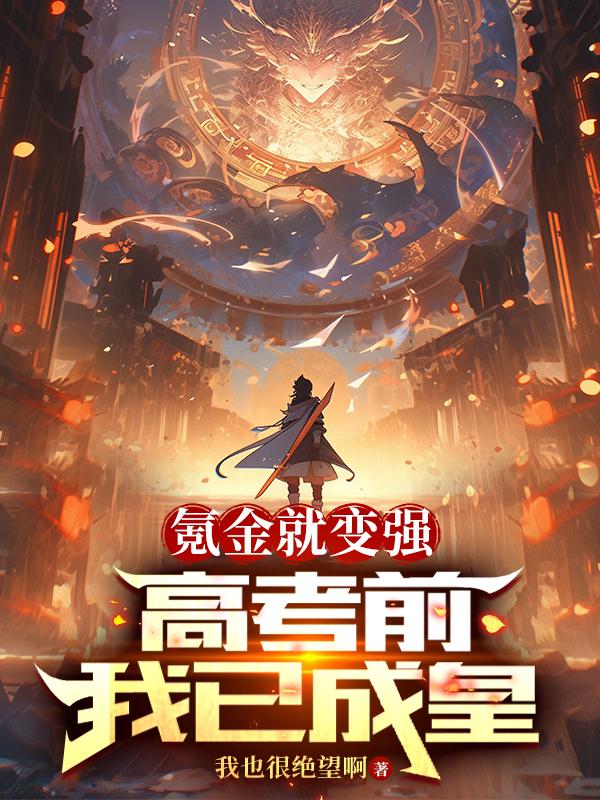第310章 河北省会变迁史
标记,心里五味杂陈,“火车拉来的省会”吗?还真是贴切!
而先辈们的反应更大,站在1840年后风雨飘摇的晚清,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抚须长叹:“保定为直隶中枢两百载,然天津开埠通商,西人货轮云集,铁路电报渐成,实为北方洋务枢纽。省会迁津,非为弃保定之厚重,实乃借津门之利,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们眼中,省会迁至天津是拥抱近代化浪潮的必然选择,唯有依托天津的港口与工业,才能引进西洋器械、培养新式人才,实现“自强”“求富”的抱负
民国时期的实业家目睹省会在平津保之间频繁更迭,拍案而起却尽显无奈:“省会三载两迁,公文政令朝令夕改,铁路运费忽涨忽跌可如何是好!”
他们深知,政治中心的不稳定直接冲击着商业秩序。天津的工厂刚适应政策,转眼省会北迁北平,原料运输路线被迫调整;保定商人刚打通省内渠道,省会又迁回天津,市场布局全盘打乱
有人痛心疾首:“若省会稳定,河北实业何至于裹足不前!要不我们按照后世经验,提前将省会定在石家庄吧?”
其他人无奈回复,“你怎么确定京广、石太、石德三条铁路干线能如同后世一般修好,能像后世一般带动石家庄这个小小的村落起势?这其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经历战火的抗战老兵抚摸着伤疤,声音哽咽:“当年省会在保定,日寇铁蹄踏破城门;流亡途中,省政府辗转千里,我们连个稳定的后方都没有!”
在他们记忆里,省会的颠沛流离是民族苦难的缩影。从保定沦陷到省政府西迁,从天津再陷敌手到漂泊西北,每一次迁移都伴随着战火与牺牲。他们或许会颤抖着说:“若有一座坚实的城市作为依托,我们定能多杀几个鬼子!”
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代表握着扳手,眼神坚定:“石家庄好啊!铁路四通八达,煤矿铁矿就近供应,建工厂、搞生产再合适不过!”
当省会迁至石家庄,他们看到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希望。石家庄凭借铁路枢纽优势,汇聚资源,纺织厂、机械厂拔地而起,“火车拉来的城市”真正成为驱动河北工业发展的引擎。有人高呼:“这一迁,咱们河北的工业化之路走稳了!”
如今的河北青年站在石家庄的CBD,望着川流不息的高铁与高楼,会自信地说:“省会变迁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时代的机遇!石家庄从村庄到省会,见证了中国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跨越。”
他们既传承着保定的文化底蕴、天津的开放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4页
相关小说
- 龙戒的使命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缘来灬如此)的经典小说:《龙戒的使命》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
- 773405字11-13
- 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吾的网兜里没有渔)的经典小说:《快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最...
- 1627559字07-06
- 淌入河流
- 淌入河流章节目录,提供淌入河流的最新更新章节列表。
- 582637字10-21
- 超高智商五人帮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绛云漫卷)的经典小说:《超高智商五人帮》最新章节全文阅读...
- 476074字09-28
- 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箭心)的经典小说:《重生了,谁还见义勇为啊?》最新章节全文...
- 525588字12-21
- 氪金就变强,高考前我已成皇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我也很绝望啊)的经典小说:《氪金就变强,高考前我已成皇》最...
- 1967196字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