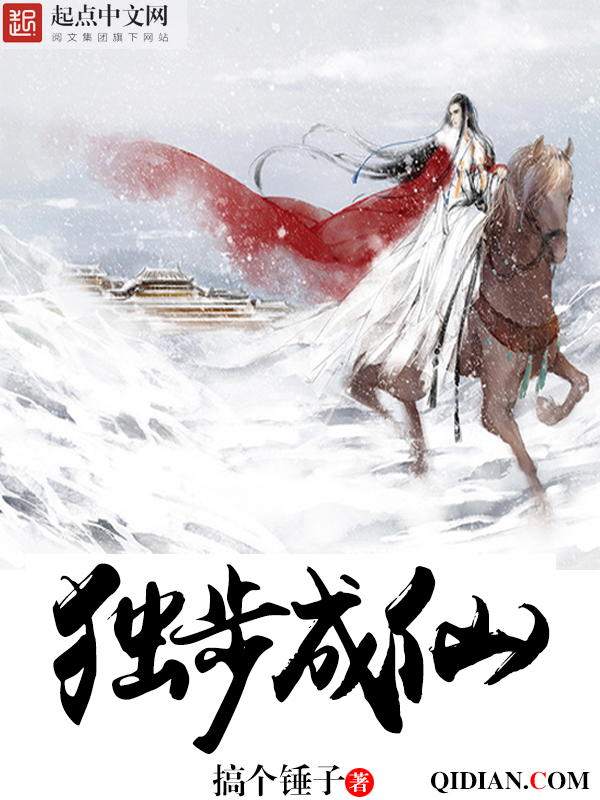第16章 西征纪实(八)利益捆绑(中)
人并不清楚沙俄的爵位体系,只知道沙皇以下最高爵位乃是“大公”,而大公以下的爵位他却一无所知,还以为跟大明一样,因此当时许下诺言,将“苏兹达尔大公”提前许给了他。
由于在奥卡河畔的决定性大胜,俄罗斯国内一时无人敢于对此表达质疑,可是等到贵族品级改革,额尔德木图看了报告才知道这事闹了乌龙——俄国制度与大明不同,他们的贵族制度本质上是学的欧洲那一套。
欧洲的“大公”其实是三种不同概念的集合体,其差异堪比伏尔加河与多瑙河。首先是以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为代表的Archduke(Erzherzog),这个源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专属于皇室直系成员,如同后来沙俄皇子必然获得“大公”称号一般,是纯粹的血缘标识而非领土象征。正如腓特烈三世将奥地利大公头衔合法化后,它便化作哈布斯堡王冠上的金丝,只缠绕在嫡系血脉之间。
其次是拿破仑时代兴起的Grand Duke(Gro?herzog),这类大公往往是独立公国的统治者,其地位介乎国王与普通公爵之间。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曾以此号令亚平宁半岛,而今卢森堡大公亨利仍在延续这种传统——他们头顶的冠冕需要领土作为底座。
当然,令额尔德木图困惑的还得是斯拉夫世界的Grand Prince(Великийкня3ь),这个源自基辅罗斯时代的称谓最初属于割据一方的君主,却在伊凡雷帝改制后沦为皇室子嗣的装饰品。
正如莫斯科大公的权杖最终化作沙皇权杖上的雕纹,这种大公头衔已与封地无关,更像是嵌在留里克或者后来的罗曼诺夫家族徽章上的红宝石。
如果说大公是凝固的权力琥珀,那么“亲王”(Prince)就是流动的水银。在德意志体系里,Fürst(领主亲王)与Prinz(血缘亲王)的区隔犹如易北河的两岸一般被明确区分——前者是拥有实地的封建主(如列支敦士登亲王),后者仅是王室血统的证明(如普鲁士王子)。这种差异在汉语翻译中常被抹平,就像把“万户侯”与“皇太子”都称作“殿下”一般,其实是有问题的。
至于英国王室的“威尔士亲王”则展现出另一种维度:它既是王储专属的进阶阶梯,又是征服者对被吞并土地的象征性统治。与此类似的还有西班牙王储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封号,这里就不一一拆解分析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不过,这种头衔在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5页
相关小说
- 帝御万界
- 一颗神秘的黑珠,揭开了自太古时期的惊天布局,人族大帝,妖族妖皇,灵族灵祖,魔族魔君...
- 150984字10-04
- 苍穹之破晓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逸云青山)的经典小说:《苍穹之破晓》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
- 2063773字06-09
- 割鹿记
-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谁人不想去长安。
- 3811279字07-03
- 天衍凰妃:凤逆天下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天绝山脉的宋局长)的经典小说:《天衍凰妃:凤逆天下》最新...
- 15723058字12-26
- 魔王大人,勇者他又招了
- 909747字07-13
- 独步成仙
- 七八小说免费提供作者(搞个锤子)的经典小说:《独步成仙》最新章节全文阅读服务,本...
- 15353342字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