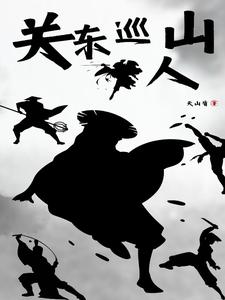第802章 克莱因
的真相,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应该更偏向于“和【大灾难】有关”。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克莱因模型”的时候,就已经恢复了彻底的清醒,所以此刻看到的东西,应该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但那可是杨佩宁啊。
从我“撒谎”到现在,应该已经过去了几分钟,就算杨佩宁的反应再迟钝,现在也该察觉到不对了。
更何况杨佩宁的反应并不迟钝,可是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那个缥缈的含混声音都没再出现过。
就像熊孩子突然安静、必定是闯了祸一样,杨佩宁这样的人,在发现情况之后无动于衷,也是相当反常的一个……
“你真的什么都没看到吗?”
含混的声音忽然响起,像飘忽的鬼魅一样突然出现。
我惊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却吃不准他现在是什么态度,只好模棱两可的回道:“我看到了……我不确定我看到了什么……”
“……”
话音落下,那个含混的声音停顿了近两秒,而等它再度响起的时候,明显多了几分迫不及待的兴奋:“你看到什么了?或许我知道那是什么。”
“线条……很多很多的线条……”
我继续“迷迷糊糊”的回道:“它们整齐排列在一起,但是构成的形状却非常凌乱,就像……就像一团没缠成球的毛线,被胡乱的扔在了地上。”
“被扔在地上的毛线……”
含混声音自言自语似的嘀咕着,语气中的兴奋被疑惑渐渐冷却,似乎正在尽力想象、我所描绘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又乐于助人的、继续增加了很多抽象的表达,却唯独没说“克莱因模型”这个标志性的特征。
就像“你画我猜”的游戏一样。
在这种抽象描述层层堆叠的情况下,即便是杨佩宁,也无法还原我所看到的那个画面——除非他之前见过类似的东西。
所以这不是拖延时间、或者转移话题,而是一场针对信息量的测试。
我想知道杨佩宁掌握了多少信息,或者说他对于我的身份、或是【大灾难】了解多少。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表述似乎有点太抽象了,接下来的近十分钟,那个含混的声音都没再出现,甚至连那种行走似的轻微律动都消失了。
要知道我此刻已经彻底清醒,再没了那种持续的节律性刺激,唯一仅剩的、那种被催眠时的恍惚感,也像潮水一样慢慢的退了下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3页